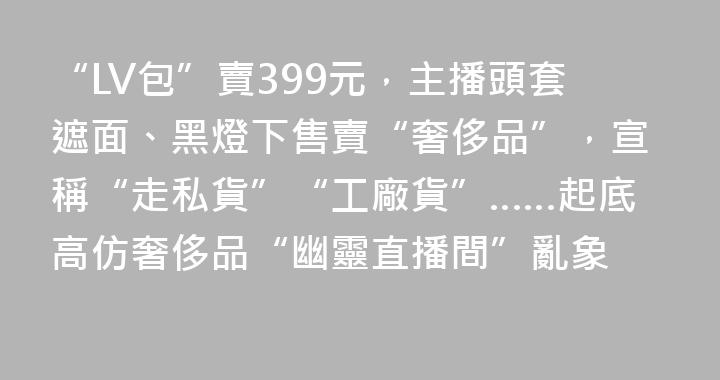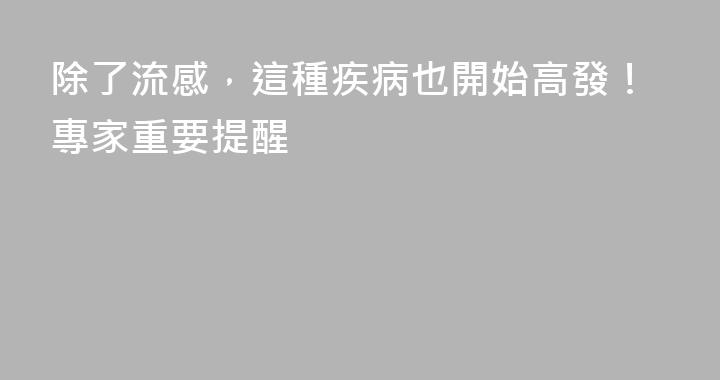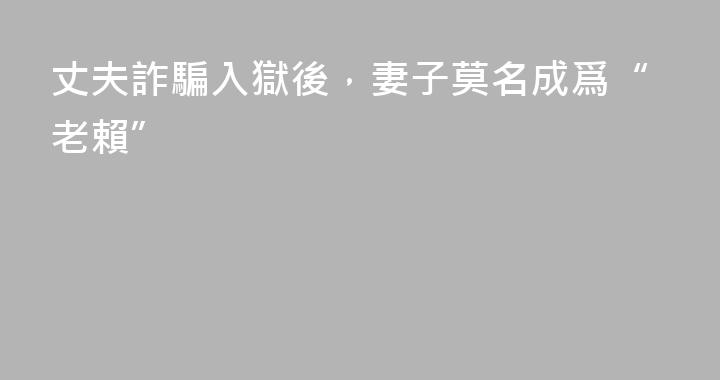10月的北京小湯山醫院秋意正濃。4個月前,35歲的徐倩在車輪下死裏逃生。她沒有想到,這個秋天自己還能有機會坐着輪椅,在湖邊看蘆花柳影、聽蟲鳥鳴唱,內心感受到了久違的平靜,彷彿人生重新活了一回。

北京小湯山醫院秋景 記者楊瑞攝
今年6月17日下午,徐倩遭遇了一場車禍。手術一週後,徐倩達到出院標準,醫生跟她強調術後康復至關重要。“我才三十多歲,既然活下來了,就必須站起來,能自理、能工作。”然而術後她無法翻身,身上仍留有引流管和未拆紗布,需每日換藥清創,家裏達不到護理要求,康復醫院成爲必然選擇。
在護士站,她拿到一份與北京積水潭醫院(以下簡稱“積水潭醫院”)合作的康復機構名單。因環境優美且離家較近,北京小湯山醫院(以下簡稱“小湯山醫院”)成爲她的首選,在這裏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康復訓練。

受訪者供圖
然而,並非所有患者都能順利找到康復機構。數據顯示,我國失能失智老人約4500萬,慢性病患者超3億,殘疾人康復需求達8500萬。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康復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每10萬人僅配備3.57名康復治療師,與國際標準要求的每10萬人口擁有50名康復治療師相差超過10倍;康復牀位佔比僅2.47%。
大醫院牀位緊張、家庭護理能力有限、社區康復資源匱乏,導致患者在急性期治療後常陷入“無處可去”的困境,不僅影響其生活質量,也加劇了綜合三甲醫院的牀位週轉壓力。
在此背景下,小湯山醫院,即小湯山康復醫院,先後與北京天壇醫院(以下簡稱“天壇醫院”)、積水潭醫院等大型綜合醫院合作成立康復中心,通過雙向轉診機制爲患者提供連續性康復服務,成爲醫療資源優化配置的探索典型。這一模式如何運作?其成效與挑戰何在?

徐倩正在進行康復訓練 受訪者供圖
01 “無縫銜接”的轉診
母親離世後,讓李虹稍感寬慰的是,母親在生命最後階段“過得還算安心”。
2023年年初,李虹母親的間質性肺炎進入終末期,無法自主呼吸,時刻依賴醫用呼吸機支撐。在北京海淀某三甲醫院住院15天后,醫生以“當前已無更多治療可開展,二級醫院條件更合適”爲由建議轉院。此前,母親已6次 輾轉北京多家大型三甲醫院,因爲無法做更多有效治療,每次住院約15天便需出院。
這次,院方協助聯繫了一家民營二級中醫醫院,並通過救護車將母親轉了過去。在這裏,母親未再被要求轉院,安穩住了兩個月直至臨終。“康復醫院條件不錯,基礎醫療設備齊全,醫護人員也專業。”李虹回憶。
車禍術後的徐倩同樣感受到了轉診的便利。7月10日,她經120救護車從積水潭醫院轉至小湯山醫院。牀位協調、入院手續、病歷流轉均無需她操心,“來了之後直接辦入院就行,醫生對我的病情也都瞭解過了。”

徐倩正在進行康復訓練 受訪者供圖
記者見到徐倩時,她剛剛結束了一天的康復訓練。如今她每天接受兩次、每次一小時的康復治療,包括電療和器械訓練。曾經臥牀不起的她,現在已經可以緩慢行走,無法活動的雙手已經可以抬放自如。
徐倩對康復中心的協作機制頗爲滿意。“積水潭醫院的主任醫師每週來查房三四次,不需要我準備病歷,醫生來之前已經掌握病情。”據她介紹,積水潭醫院的醫生會看一遍最新的檢查結果,與小湯山醫院的醫生共同制定康復計劃。每週兩次回積水潭醫院複查時,醫生也允許她直接加號就診。
天壇小湯山康復中心的運作模式與此類似。小湯山醫院神經康復科主任醫師談曉牧介紹,作爲國家神經疾病醫學中心,天壇醫院接收大量中樞神經系統損傷患者,如腦梗塞、腦出血、腦腫瘤術後等,這類患者常出現肢體活動受限、吞嚥困難、失語等功能障礙,術後或急性期後半年內的“黃金恢復期”干預效果最佳。

天壇小湯山康復中心 記者楊瑞攝
患者在天壇醫院完成急性期治療後,可直接經救護車轉至小湯山醫院神經康復中心。“患者入院後,首先會接受全面評估,包括關節活動度、肌力、平衡能力及認知功能等等,醫生根據評估結果制定康復方案,由治療師負責執行。”神經康復科主任助理徐浩明表示。
據她介紹,患者每日康復時間約2小時,項目涵蓋電刺激、物理治療、作業治療、中醫鍼灸、水療等等。每週期康復治療通常爲25-30天左右,多數患者能有明顯功能改善。
02 醫聯體模式下的“各取所需”
“綜合醫院+康復醫院”的合作模式並非新事物。
小湯山醫院黨委委員、副院長王莉見證了康復中心從無到有的過程。她指出,這一模式得益於市衛生健康委、市醫管中心的統籌部署。政策明確小湯山醫院以康復爲特色發展方向,與大型綜合醫院構建“緊密型醫聯體”,實現差異化互補。
自2017年起,國務院、國家衛健委、北京市醫管中心等多部門發文推動“緊密型醫聯體”建設。簡單來說,就是把一家大醫院和它周邊幾家小醫院/社區衛生院,像“總公司”和“分公司”一樣緊密地組合起來,統一管理,資源共享,分工協作。醫聯體內實行“雙向轉診”:小機構首診,疑難重症轉至上級醫院;急性期治療後,再回基層康復。

天壇小湯山康復中心 記者楊瑞攝
如此一來,專家“下沉”了、病情信息能共享、家門口就能看病開藥、基層醫護人員水平提高了,最終目的是實現“小病在社區,大病去醫院,康復回社區”的理想狀態。截至2023年底,全國共組建各種形式“醫聯體”1.8萬餘個,全國雙向轉診人次數達到3032.17萬,較2022年增長9.7%。
然而現實中,據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顧海觀察,因利益衝突、財務衝突、機制缺陷等因素,部分醫聯體合作鬆散,僅停留在“上級專家下來坐坐門診”的層面,檢查結果、病歷處方等信息仍未實現互聯互通,“雙向轉診”通道也不暢通。
記者走訪北京市朝陽區多家社區醫院發現,多數機構無法調取患者在二三級醫院的診療信息,需患者自行攜帶紙質病歷;也無法直接將患者轉診至大型醫院。“我們掛三甲醫院的號和患者自己掛號是一樣的,沒有優先權”,一工作人員坦言。
在小湯山醫院,“緊密型醫聯體”得到了有效落實。除神經與骨科康復外,還通過與北京兒童醫院、安貞醫院和北京中醫醫院合作,拓展兒童康復、心肺康復、中西醫結合康復等服務,醫院平均牀位使用率從60%提升至90%。

北京兒童醫院小湯山診療中心
據小湯山醫院運動康復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何件根介紹,除轉診無縫銜接外,醫院在質量管理上實行“兩院一科”模式:積水潭醫院專家每週定期參與查房與會診;康復治療師每月輪換駐點,確保服務同質化,包括統一藥品目錄與治療規範。
合作還延伸至科研教學領域。何件根表示,小湯山治療師會輪流前往積水潭醫院進行爲期六個月的培訓;雙方還會定期聯合舉辦學術會議和文獻學習活動,包括每週一次的專題學習和線上病例討論等等。
“各取所需是合作成功的關鍵。”王莉認爲,大醫院需術後康復出口,小湯山醫院則需外科技術支撐以強化康復品牌。
數據顯示,北京市康復牀位供給嚴重失衡,現有資源遠不能滿足神經疾病、骨科術後等患者需求。以腦卒中爲例,康復牀位缺口約4000張。民營康復機構雖存在,但部分機構的醫療質量和安全管理難以保障。因此,政府主導的醫聯體模式成爲破題關鍵。
“領導重視與支持同樣重要,”何件根補充,“這直接影響政策落地與醫護人員積極性。”小湯山醫院對派駐醫師給予大力後勤保障,包括提供宿舍等等,消除其後顧之憂。
03 基層康復如何“接得住”?
隨着康復醫療需求日益增長,“綜合醫院+康復醫院”這一創新模式在實踐過程中也面臨着發展瓶頸。
最直接的問題便是牀位資源不足。小湯山醫院作爲區域康復樞紐,目前擁有不到400張牀位,依然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康復需求。
此外,儘管康復中心與綜合醫院已實現檢查檢驗資料共享,但手術記錄等關鍵信息仍無法實時獲取。按規定,患者病歷需出院後7個工作日方可複印,因此康復中心往往無法及時瞭解手術細節,只能依靠人工查詢。若醫生繁忙或缺乏意願,信息獲取便可能會延遲。

北京兒童醫院小湯山診療中心
雙向轉診中,醫生溝通的及時性也是一大挑戰。主治醫生因手術繁忙或羣消息過多,往往難以及時響應康復中心的諮詢。而且轉診患者可能經歷多名醫生交接,原主治醫生不一定負責後續跟進,可能需多次週轉才能找到最初的手術醫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隱私保護與流程規範。現有醫生們交流多依賴微信等社交媒體工具,不符合醫療信息安全要求,而正式申請需經OA系統層層審批,流程冗長。這種信息壁壘影響了康復治療的連續性與精準性。
談曉牧建議從機制與技術層面雙管齊下:一方面完善醫醫溝通機制,建立標準化信息查詢與反饋流程,明確響應時限,減少信息週轉環節;另一方面,亟需構建符合醫療安全標準的專用平臺,支持手術記錄、影像資料等關鍵信息的實時加密傳輸,提升雙向轉診的協同效率。
何件根從事康復工作已有近20年,相比於合作技術性問題,他更關注整個康復行業的系統性問題。根據醫保政策規定,公立康復醫院的住院週期多爲3-4周,之後患者需轉向社區或居家康復。然而,多數社區醫院未設獨立康復科,相關服務多掛靠中醫科,僅能開展鍼灸、推拿等基礎項目,缺乏現代設備與專業場地。
人才短缺問題更爲嚴峻。康復科主任多由內科、外科或中醫科醫生轉崗,科班出身的康復醫師稀缺。同時,康復科收入在醫院內處於較低水平,科室薪酬吸引力不足;加之執業門檻不足,非康復專業醫生也可以直接從事康復工作,進一步加劇了人才流失。
而患者對基層康復信任度低,形成了惡性循環。何件根觀察發現,患者普遍認爲社區醫院水平有限,更傾向於前往三甲醫院,導致基層資源閒置而大醫院擁堵,且去基層醫院多傾向於開藥或中醫理療,而非操作性康復。
針對人才缺口,何件根建議從課程設置、實習安排、專業劃分、進修教育等多角度加強培養,“目前醫學本科教育中康復醫學課程較少,康復醫學還屬於年輕學科”;其他專業轉崗或跨專業從事康復醫療,建議進行專科化轉崗培訓,建立康復醫療的准入門檻。
“搭建學科梯隊需要5-10年,硬件跟上容易,最難的是人才建設與患者信任。”何件根總結道。
(應受訪者要求,徐倩、李虹爲化名)
採訪:楊瑞 劉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