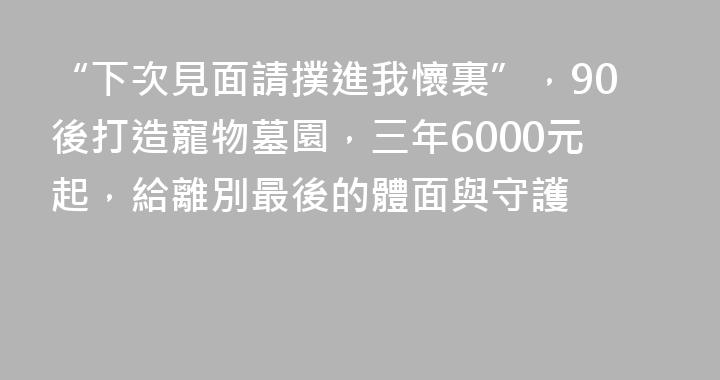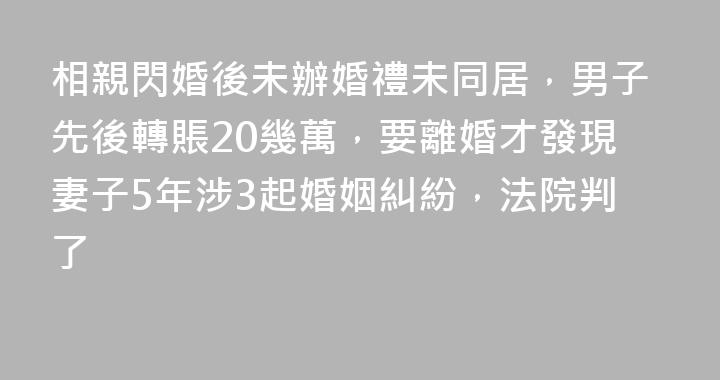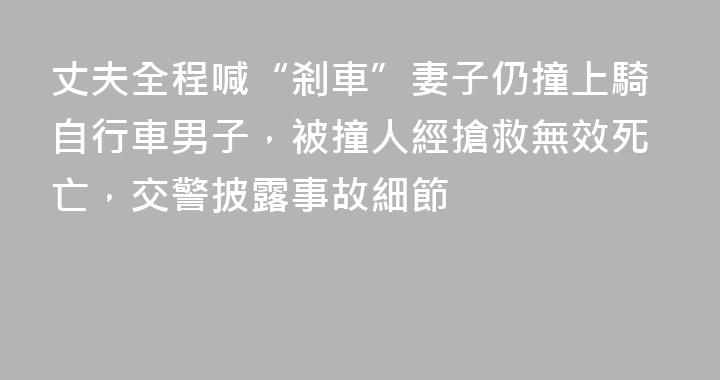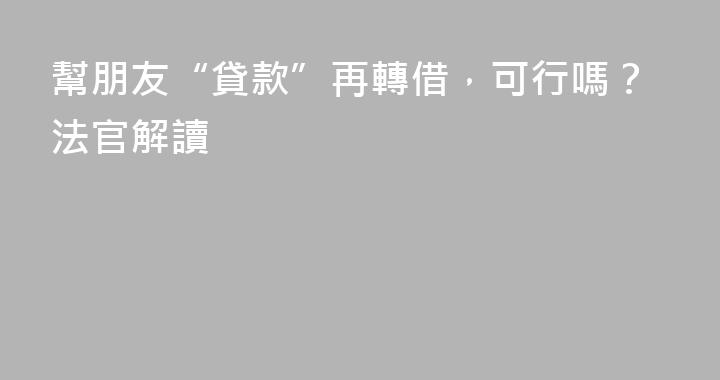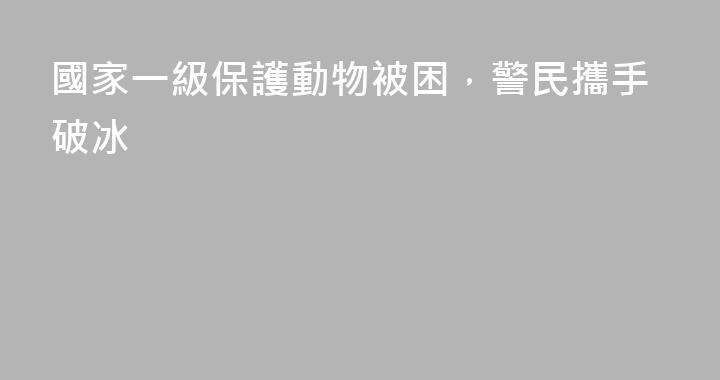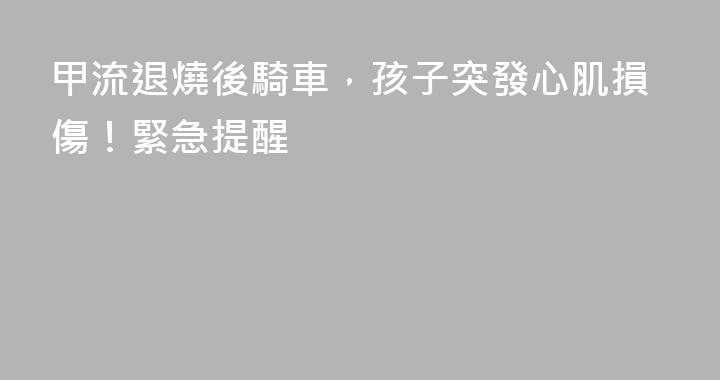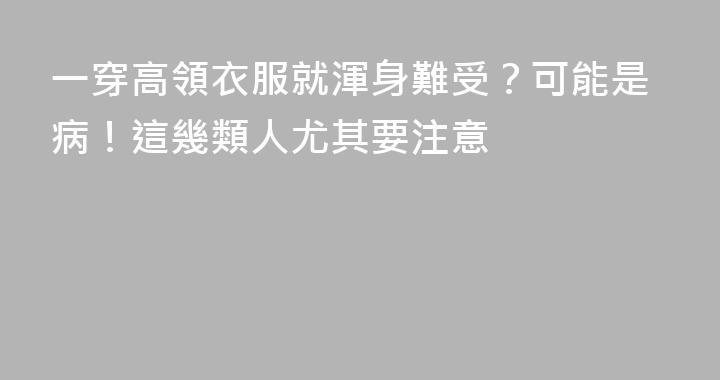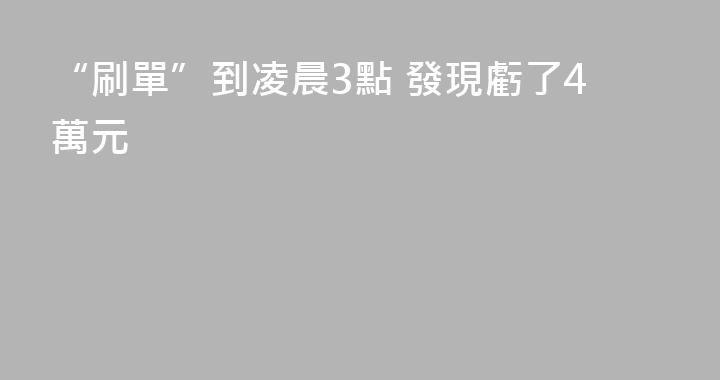我的孩子14歲,當我叮囑“快點寫作業”,他回:“那咋了”;我提醒“飯菜要涼了”,他還是:“那咋了”;我嚴肅地說“好好說話”,他依然拖着長音:“那~咋~了~”。
“我不喜歡孩子的言行舉止被網絡所裹挾。”這位媽媽堅定地表示。
10月19日,“文小叨老師”發佈的一段視頻也在社交平臺上道出了衆多家長和老師的心聲:“喜歡說這些話的是偷懶的人,因爲只要說這些話,他就可以停止思考。當孩子腦袋裏只有網絡熱詞時,那些優美的好的語言都被覆蓋了,成語、諺語,歇後語都不會用了。”
“包的”“那咋了”“你個老六”“六百六十六”……這些網絡詞彙是如何成爲一些孩子下意識的習慣並流行起來的?
“只要有手機都會說啊。”初三學生小童的一句話,點破了現實,“有時候就是覺得好玩,大家都說,你不說就顯得很另類。”
這些詞來自哪裏?孩子們爲什麼喜歡說?除了說這些,還能說什麼?
這兩天,就此話題,我們走進了多所中小學。
同學傳同學,
這些詞很流行
“包的!”“如何呢?”“那咋了”“六百六十六”……這些詞在小學生羣體裏確實挺流行。
“媽媽說寫完作業可以玩一會兒,我就會說‘包的包的’!”杭州某小學二年級的瑞瑞經常在需要表述“必須的”這個語境時使用網絡熱詞,他身邊的同學紛紛點頭,表示也經常會使用這個詞。
天天同學回答得很快:“和同學開玩笑時會說,大家都覺得好玩。比如有人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底下就會有人小聲說‘演都不演了’,然後大家都偷偷笑。”
這些網絡熱詞的傳播路徑出奇一致——同學傳同學,高年級傳低年級。
四年級的小雪說:“我們小區有個羣,裏面五六年級的哥哥姐姐經常發這些詞,看着看着就會了。”問小雪是否知道這個詞的原始含義,她搖搖頭:“大家都這麼說,覺得挺酷的。”
“有時候聽不懂同學們在說什麼,接不上話會感覺難受。”另一個同學補充,“我只有一個能打電話的手錶,四年級以後媽媽不讓我玩手機。”在小學階段,絕大部分家長都會嚴格管控孩子們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這類孩子往往對網絡熱詞知之甚少。
“我做完作業,媽媽就讓我玩半小時手機。”一個男生說,他在社交平臺上學會了不少網絡用語,“我知道什麼時候能說,什麼時候不能說。”
“我從來不說這些詞。”婷婷表示,“說了就會被媽媽說。”她身邊的同學也附和:“有些詞聽着不太好,我們不能說。”
杭州東城外國語實驗學校的李老師教語文11年,據她觀察,現在很多家長對網絡用語比較謹慎,“一旦發現孩子說這些詞,會立即制止”,因此班上真正經常說網絡熱詞的孩子不多。
李老師說,低年級學生對網絡用語的分辨力較低,她平時也會特別注意引導孩子正確使用詞彙。
這些梗用多了,
表達力會匱乏嗎
“我們班很多人說的!”杭州某中學707班的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
坐在第一排的小徐同學告訴記者:“這些詞並不是最近纔開始流行的,有一陣子了,一出來就開始傳播,一傳十十傳百,轉眼全班都會了。”
調查顯示,該班25名學生接觸網絡熱詞全部通過同學日常交流自然習得。“用這些詞聊天特別有梗。”小丁同學晃着腦袋解釋,“剛入學那會兒,說句‘尊嘟假嘟’立馬就和同學拉近距離了。”課間休息時,“包的”“天塌了”“尊嘟假嘟”等詞此起彼伏。
初中生們認爲,這些濃縮的表達能瞬間傳遞情緒,但他們也強調了使用邊界:“我們很少在老師面前說,寫作文更是嚴格區分場合。”孩子們心照不宣地捂嘴笑:“語文老師看到‘栓Q’會扣分的!”
網絡熱詞用多了會不會思考力下降?或是表達力匱乏?
班主任徐老師觀察到,學生在正式場合能自覺切換語言模式:“早讀課從沒人說網絡熱詞,但在操場打球時‘這操作666’之類的感嘆就很自然。”
副校長陳海紅則辯證看待這一現象:“互聯網原住民接觸新詞彙無可厚非,但需要引導適度使用。”她舉例,當所有驚歎都被簡化爲“絕絕子”時,孩子們可能逐漸喪失描述“看到錢塘江大潮時那種心跳加速的震撼”的豐富詞彙。
據介紹,西興中學將藉助主題晨會展開“傳統成語VS網絡熱詞”討論,在包容創新表達的同時,培養學生精準使用語言的能力。正如陳校所言:“既要擁抱時代語言特色,更要守護漢語的豐富性與精確性。”
網絡熱詞不斷迭代,
堵不如疏
“有時候孩子們嘴裏蹦出來的網絡用語,我們都聽不懂。”富陽一所小學的音樂老師張老師說,孩子們就像一塊嶄新的海綿,每當網絡上有新的熱詞興起,他們總是最快吸收和運用的人。
而在課堂上,這樣一句網絡熱詞很可能成爲學生之間的暗號。
有一次當她按慣例詢問孩子們是否聽懂自己的講解內容,有一位性格活潑的同學突然喊道“聽不懂思密達”,引發了班級裏的鬨笑聲。
面對這樣的行爲,張老師進行了制止:“我明白孩子們只是想活躍一下氣氛,但是課堂紀律還是要認真遵守的。”
台州某小學的王老師也有同樣的煩惱,孩子們的口頭禪常常變化,她時常面臨“接不住梗”的情況。
王老師說,現在學生們愛用的部分熱詞中帶有不文明的用語,比如“你個老6”“我嘞個騷剛”,並不適合作爲口頭禪使用。
和學生們溝通後,王老師也知道孩子們其實並不知道詞語的含義,只是覺得跟着同學們說很有趣。“作爲老師,我們會及時引導學生們停止不恰當的用語。”王老師說,之前有二年級的學生把這些網絡用詞寫進了作文裏,語文老師馬上聯繫了家長,共同對孩子進行勸導。
老師們都提到,孩子們就像一張白紙,會在現實和網絡世界之間染上色彩。對於他們愛講網絡熱詞的行爲,更建議堵不如疏。
大多數家長則對此持開放態度,既不贊成也不反對。
有家長評論,每個時代的青少年都有屬於自己的“黑話”。70後的“震了”“派”,80後的“酷”“帥呆了”,90後的“囧”“雷人”,到如今的“包的”“那咋了”,變的只是具體的詞彙,不變的是青少年通過語言尋找認同、建立羣體的需求。
一位90後家長認爲,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讓當下青少年的“黑話”傳播速度呈指數級增長,一個熱詞可能在一夜之間風靡全國校園,又在幾個月後悄然過時。“我們小時候說‘恐龍’‘青蛙’,爸媽也一頭霧水。現在輪到我們聽不懂孩子的話了,這才理解當年父母的心情。”
潮新聞記者 戴佳軼 方力見習記者 呂惟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