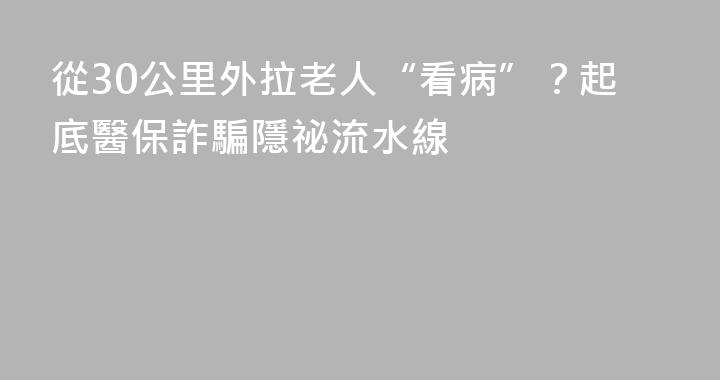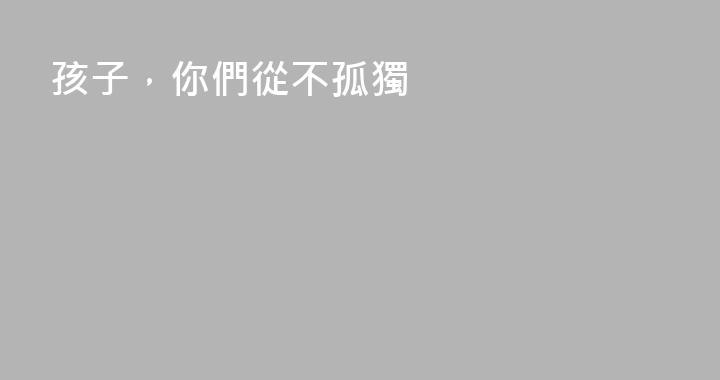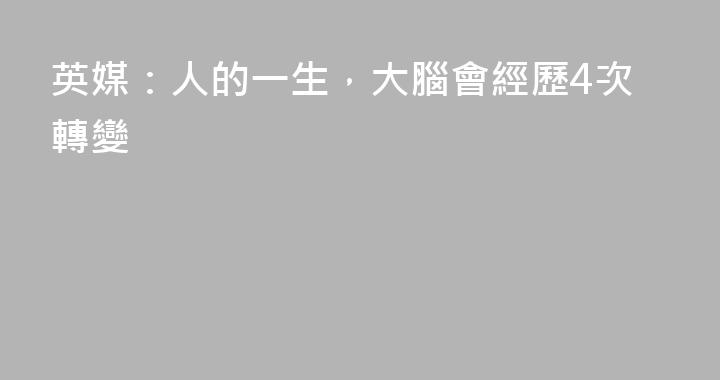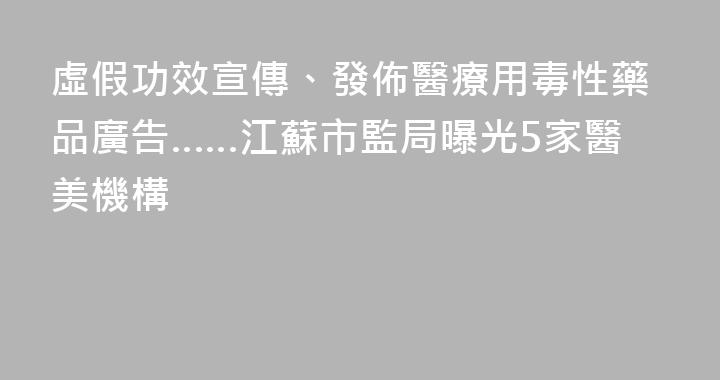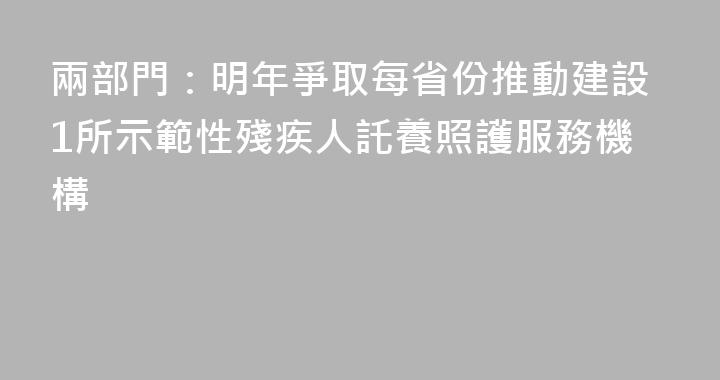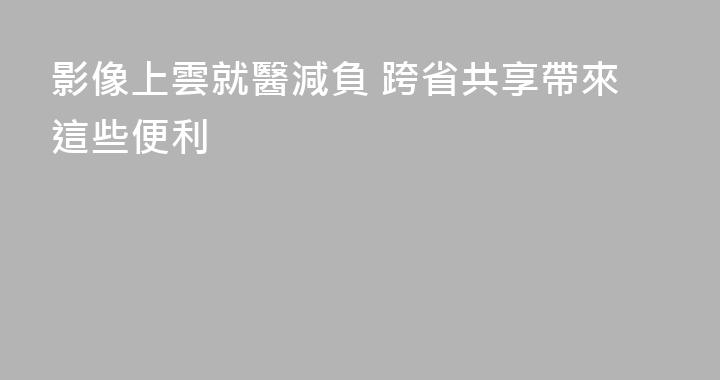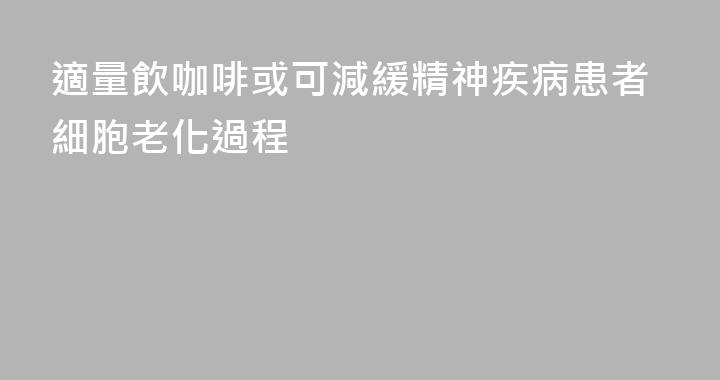我是遼寧大連“臨時保鏢團隊”發起人,大家都叫我阿凱。
我還記得我接的第一單“外包兒子”生意。敲門後,迎接我們的是一道門縫,以及門縫後一雙充滿警惕和審視的眼睛。
“我們是您妹妹請來的,她不放心,託我們過來看看您。”我儘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溫和,但門後的老人沒有回應,只是沉默地將門拉得更開了一些,讓我們進屋。
75歲的李奶奶平時一個人住在大連市的一個老小區,唯一的兒子車禍離世,老伴也早已故去。她的妹妹遠嫁別處,通過短視頻平臺聯繫上我們,希望團隊能夠代替她,多去看看孤單的姐姐。
一名孤寡老人的世界可以小到什麼地步?從牀到衛生間,再到廚房冰箱,失獨且喪偶的李奶奶幾乎每個日夜都是在這個狹小的一居室內度過的。我們幾個人進屋後,屋子立刻顯得逼仄起來。更“可怕”的是,屋裏安靜極了,似乎掉根針都能聽得見。兒子與丈夫的相繼離去,好像兩把剪刀,剪斷了李奶奶與外部世界的連接。當時我就想,這份委託的意義,或許就是爲老人的生活重新注入一點當下的、流動的“聲響”。
第一次上門時,無論我們說什麼,老人都只是淡淡地回上幾句。從上午10點到下午6點,我們爲老人做了一頓午飯、幫老人打掃了房間,其餘時間則是試圖和她聊天。
起初的兩次探訪,都是在近乎尷尬的安靜中度過的。老人不主動說話,對於我們的到來,既不歡迎,也不牴觸。我們只能從家務做起:打掃積灰的角落,清洗許久未用的碗筷,疊好沙發上隨意堆放的衣物。
隨着上門次數多了,李奶奶逐漸卸下了心防,態度愈發軟化,明顯的信號便是——她開始絮絮叨叨地講起了往事,講她經歷過的那些歲月、講她因車禍去世的兒子、講她病故的老伴。
這是一單價格在2000元的委託,持續一個月,我們一共探望了5次,每次待至少6個小時。在最後一次上門探望結束時,李奶奶眼圈泛紅。我們心有不忍,向老人承諾,下次路過小區一定再上樓看看。
委託人還有遠在國外不能頻繁歸家的子女。
比如今年70多歲的張爺爺,與老伴住在大連,委託人正是定居在國外的子女。接單時,老人的子女在電話裏反覆叮囑到我都覺得他們囉唆,主題只有一個——張爺爺脾氣火暴,不僅對家人如此,與鄰里間的關係也常年緊張。
第一次上門時,老人態度果然很差——“你們來幹什麼?我好好的,不需要人看。”老人坐在沙發上,語氣冷漠。
這次委託持續了一個半月,直到委託時間過半,我們才慢慢了解了事實的全貌:老人之所以與鄰里關係緊張,始於鄰居細碎的、帶刺的非議。子女遠居國外成了鄰居口中的談資,“掙大錢忘了爹孃”“孩子在國外,生了不如沒生”,這些話語,讓向來爭強好勝的老人聽多了難免心中鬱悶。
委託期內,我們一共上門了8次,陪老人聊天、散步、買菜,見到鄰居就說自己是老人的“乾兒子”。當鄰居們看到總有幾個身形健壯的年輕人提着東西上門,陪老人聊天、打掃衛生後,背後的非議逐漸少了,老人的情緒也平穩了不少。
子女外出務工、中年喪偶喪子、養老體系尚不完善……對於不少老人來說,這樣的晚年生活是一場漫長的鈍痛。
我始終記得那位在牀上癱瘓了近40年的修理工。一場突如其來的工傷事故,讓他下半身完全癱瘓,生活無法自理。委託人是他的弟弟,訴求很明確:解決護工偷懶問題。原來,負責照料老人的護工看老人無兒無女,在日常照料上,不會主動詢問老人的如廁需求,往往是等到老人失禁後才進行清理。在飲食方面,她通常一兩天做一頓飯,讓老人反覆喫剩飯。
我們團隊在兩個月內前後共上門了10次,要留意牀單是否乾爽、平整,房間內有沒有異味,在護工做飯時走到護工身邊監督她是否用心。若是看到護工在老人有需求時還在玩手機,我們會及時提醒護工,看着護工完成護理工作。
據老人弟弟反饋,護工的行爲有所改善,比以前勤快了一些,至少平日裏無事的時候不會像過去那樣直接躺在沙發上,有時還會陪老人聊天。
人老了,脾氣有時會變得像孩子一樣,容易因爲小事耿耿於懷,將問題放大,再加上他們往往不願主動溝通表達,容易讓遠方的親人擔心誤解。
住在大連某養老院裏72歲陳阿婆的情況就是如此。
據委託人描述,住在陳阿婆隔壁的老人總在半夜將電視或音樂的音量故意開得很大,嚴重影響陳阿婆睡眠。團隊介入後發現,這原本是個誤會。那位老人之所以將音量開得很大,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因爲她本人聽力嚴重受損。團隊爲隔壁老人買了副耳機,問題迎刃而解。令人欣慰的是,這次之後,兩名曾因誤會產生隔閡的老太太,關係反而變得非常融洽。
我們服務過的這些老人,無疑是不幸的,但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又是幸運的。至少還有人牽掛着他們,願意付一筆不低的費用僱傭他人扮作“臨時兒子”前往探望。可也有一些老人,到了晚年,一個家人和朋友也沒有了,我有時候會忍不住想,那些老人的晚年光景又是什麼樣的呢?
(本報記者 趙麗 本報實習生 宋昕怡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