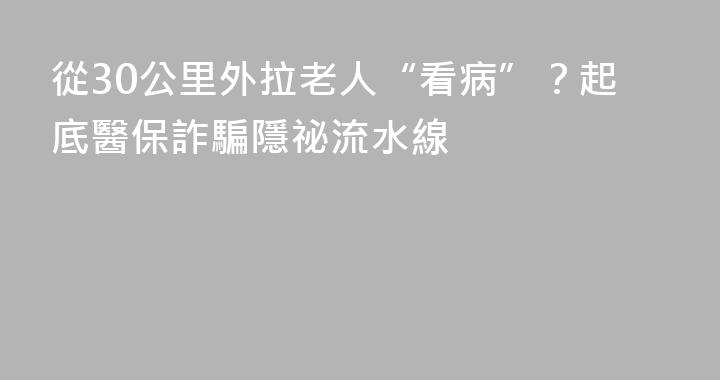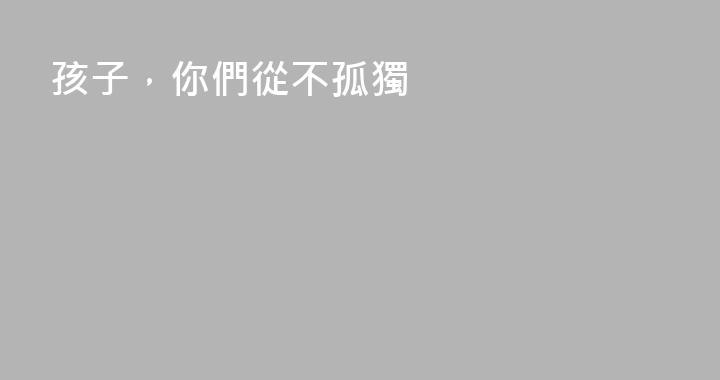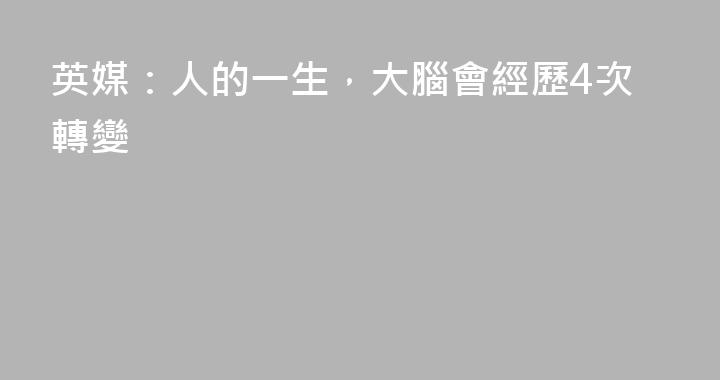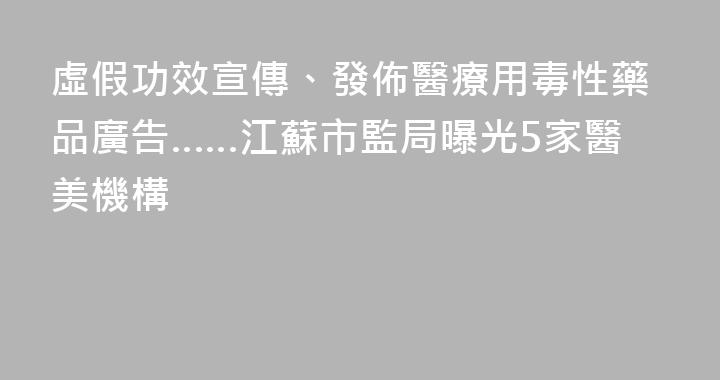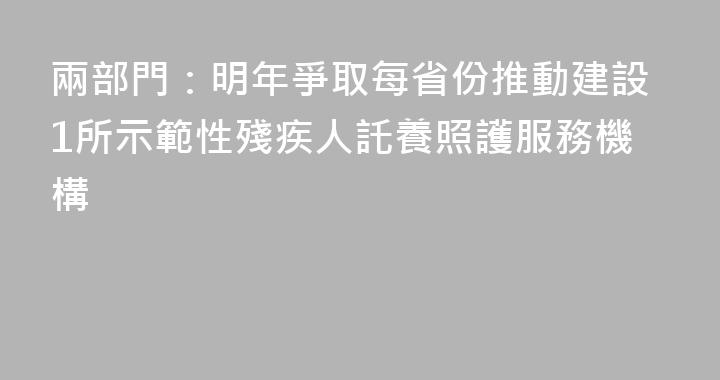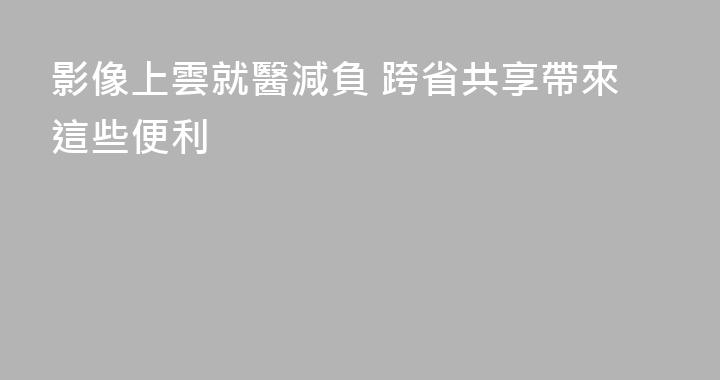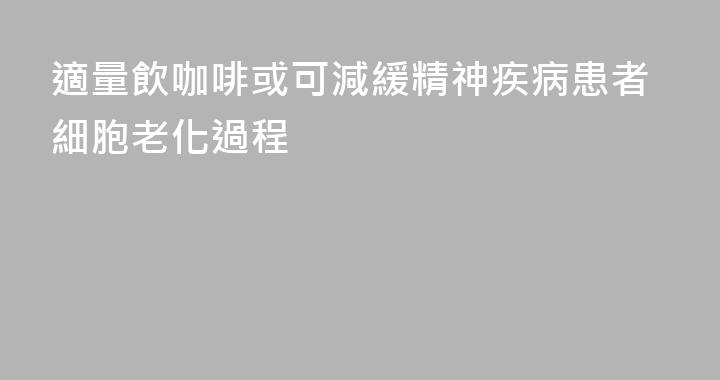某日出門診時,一位村民問我:總是拉肚子,可以煮“老鴉酸”來喫嗎?我愣了一會兒,纔想起,我們惠州人把酢漿草叫“老鴉酸”,老鴉指的是烏鴉。在粵東,還有叫它“鵓鴣酸”的。此外,聽說有的地方叫它“斑鳩酸”。酢漿草的根莖是酸的,我小時候嚼過,名字裏的“酸”不難理解。可是,爲什麼它的三個俗名裏都有鳥類呢?是否因爲葉片的形狀像鳥的翅膀?我至今沒有弄明白。
從接觸中藥學的時候起,我就發現,不管學名還是俗名,草藥的名字總是可親可愛的。比如藥食兩用的馬齒莧,我們叫它“老鼠耳”。馬齒莧、老鼠耳,都是以葉子的形態來命名的。它的葉片扁平、小巧,呈倒卵圓形,很像馬的牙齒,又很像老鼠的耳朵。馬齒和鼠耳,兩種毫不相干的東西,竟被用來指代同一種植物的葉子,想想真是既奇怪又合理。
再說家喻戶曉的魚腥草,客家話叫“狗貼耳”,四川方言把它的根叫“折耳根”。魚腥草,是以氣味來命名的。喫過它的人,一定忘不了那股獨特的魚腥氣。狗貼耳、折耳根,是以葉子的形態來命名的。它的葉片末端尖尖,呈卷折的心形,儼然一隻狗耳朵。
金櫻子,我們叫“糖罌子”,罌子就是大腹小口的瓦罐。別處也有叫“糖罐子”的,含義相似。顧名思義,糖罌子外形似罐子,味道甘甜。如此甘甜,自然要長滿刺來保護自己。因此,我們又叫它“糖罌簕子”——帶刺的糖罐子。作爲野果子,它成熟後色澤金黃,綴滿山間溪旁,給我們留下了甜蜜的童年回憶。曬乾後,又成爲一味難得的“甘口良藥”,讓人免受苦味的折磨就治好了病。就連患有遺尿需要服用它的小兒,也無須家長強灌,自己端起湯碗就喝下了。
益母草的名字更多。其一爲“益母草”,以功效命名,有益於女子。雖也可用於男子,終歸是女子用得多。其二爲“九重樓”,以花的形態命名。淡紫紅色的小花圍成一圈,重重而上,形似塔樓。其三爲“籠牀稈子”,指的也是花穗,一層層的,就像蒸糕點的籠屜。其四爲“茺蔚”,意爲充盛密蔚。記得有年初春,媽媽在老屋後隨手撒下一把益母草種子,就去了城裏。等夏天回來一看,齊膝的青草竟已鬱鬱蔥蔥。
益母草還叫“坤草”。正是那年夏天,媽媽望着那片益母草,感嘆道:真是賤生。她說的賤生,並非貶義,是指植物無論在多惡劣的環境下,都能繁茂生長。行醫數年後,再回想起這個場景,感觸頗深。這種其貌不揚又極具生命韌性的植物,不但像女子一樣生長在大地的各個角落,還消除了多少女子的病痛呢。乾爲父,坤爲母。坤草,意即大地之草、母親之草。這樣“大”的名字,安在它身上,卻一點也不爲過。
講起來,草藥好聽的名字太多了。以時間命名的,有夏枯的“夏枯草”,忍冬的“忍冬藤”;以形態命名的,有莖節膨大的“牛膝”,白絲披散的“白頭翁”,斷面滲出紅汁的“雞血藤”;以功效命名的,有可以防風的“防風”,可以明目的“決明”;以顏色命名的,有紅的紅花、赤芍、丹蔘,黑的玄蔘、黑醜、墨旱蓮,還有青蒿、黃連、白芷、紫菀;以滋味命名的,酸棗仁、甘草、苦蔘、細辛,酸甜苦辣應有盡有,甚至有“五味子”,我曾因好奇嘗過,真是五味雜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