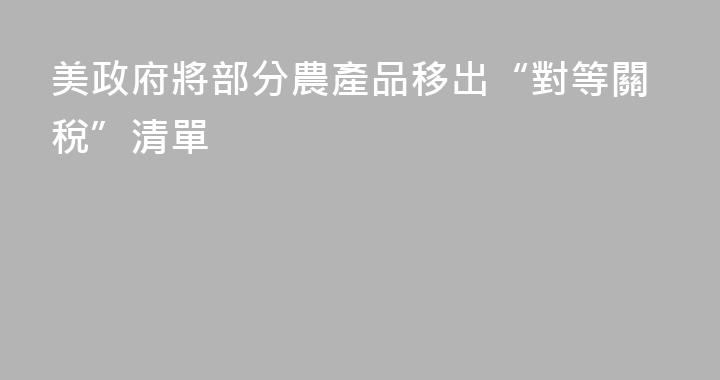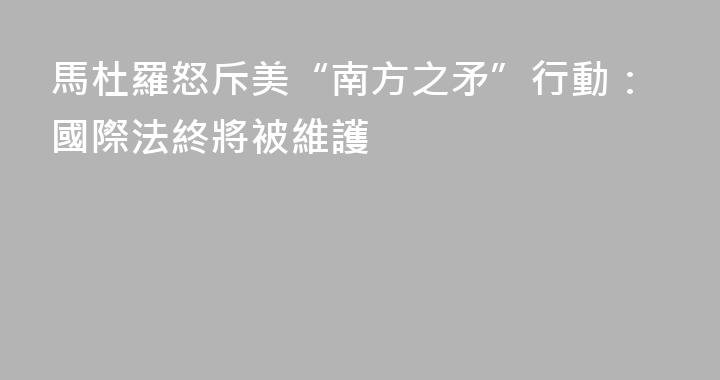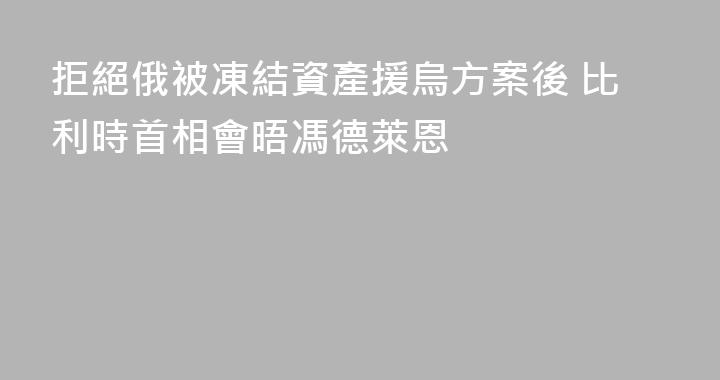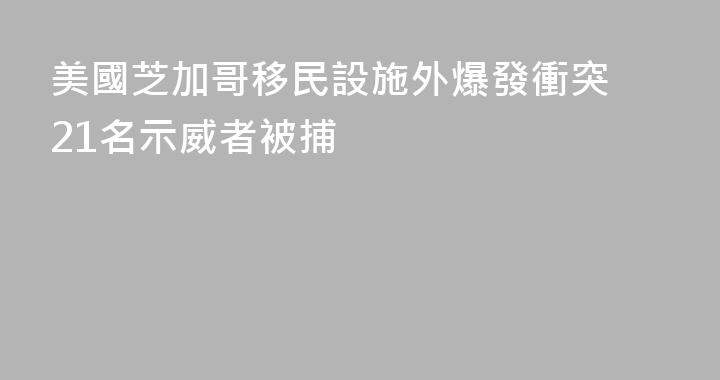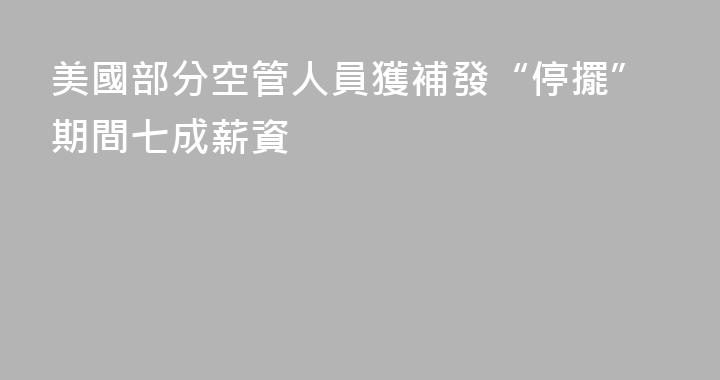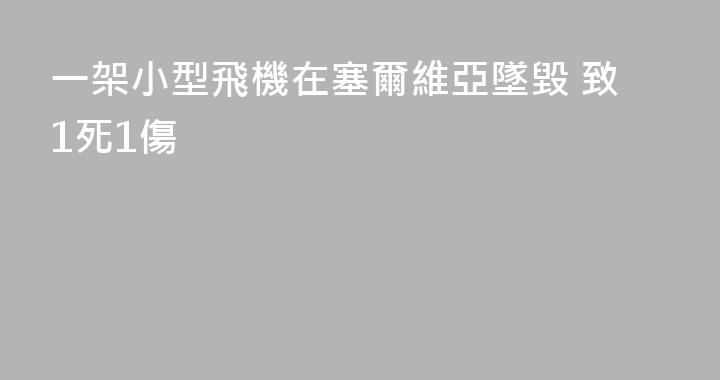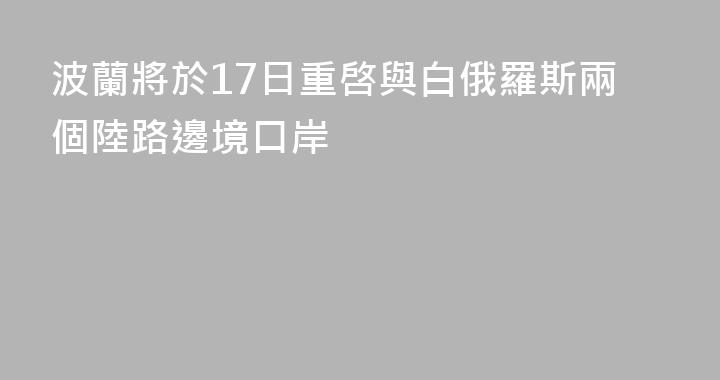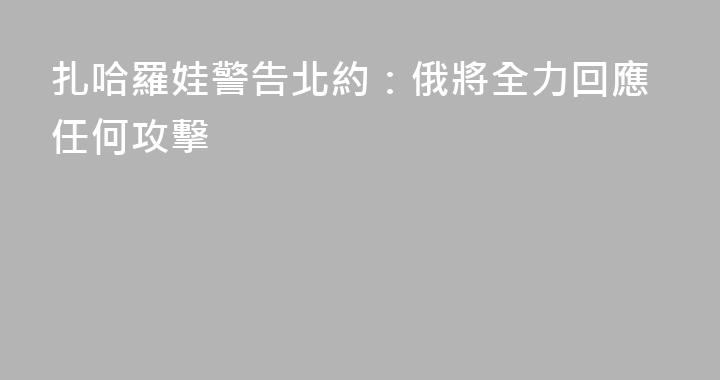【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徐劉劉 張冬瑾 姜李 李予澈 董鳳】編者的話:10月14日,由國務院新聞辦、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辦的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在上海拉開帷幕,約500名海內外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圍繞“世界視野下的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主題展開深入交流研討,共同爲推進中國學發展、推動文明互鑑貢獻學者力量。在大會召開之際,《環球時報》“海外看中國”工作室聯合北京外國語大學、國家圖書館、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語言大學,推出“我與中國的學術之緣”系列訪談。第一期邀請5位中外學者共同探討中國學的世界意義與時代價值。他們分別爲: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西平、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安樂哲、國家圖書館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資料中心副主任尹漢超、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白樂桑與伊朗國家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納思霖。
如何“跳出中國看中國”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漢學》名譽主編張西平的著作《中國與歐洲早期思想交流史》被廣泛視作西方中國學研究的必讀書目。在訪談中,他表示這本書主要是撰寫歐洲和中國早期哲學和宗教的交流情況,推動中歐重新回到平等對話原點。他在書中的基本觀點是通過歷史經驗來告訴歐洲,應以文明互鑑增進交流和理解,並避免衝突。
張西平認爲,隨着全球化的發展,任何民族史都不再由本民族獨家語言書寫,因爲歷史是在相互交流中發展的。“西方漢學經歷了遊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專業漢學三個階段。”當代漢學和中國學興起後,紐約、倫敦、巴黎的漢學家開始用英文、法文來研究中國。因此,漢學研究、海外中國學的存在,標誌着中國學術已經是世界性學術。
展望未來的中國學研究,如何從“從局部看中國”“就中國論中國”,逐步走向“跳出中國看中國”呢?張西平引用梁啓超的話說:“在中國研究中國,在亞洲研究中國,在世界研究中國。”他表示,“中華文明有人類共同的普遍性價值,但也有特殊性,比如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多民族國家,這與歐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主張的‘國家是單一民族爲主體’的提法不一樣。”所以,想要全面瞭解中國,一定要將長時段的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全面、客觀地理解中國。
作爲美國最知名的漢學家,費正清最重要的理論就是“衝擊—反應”論,即中國受到外部影響而發展。但他的學生柯文不同意他的觀點,提出從中國內部視角出發,關注本土因素與能動性。張西平提到,從晚明張居正改革以後,中國就開始實行以白銀爲國家貨幣的經濟制度,有些學者認爲這是中國近代化的起步。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認爲,中國自身現代化過程源自持續的內生性發展,只是發展的速度慢於歐洲。“中國自身的內生動力是很強的,不能說中國的發展是完全停滯的,這是西方19世紀對中國的錯誤理解。”他表示,中國當下的國家體制與歷史上的大一統有着密切的關係,不瞭解自秦以來郡縣制的建立以及歷代統治者所追求的大一統的國家管理,就無法理解當下的中國國家形態。
張西平說,在研究中國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走出當前西方對中國的不客觀描述。“漢學家有別於一些西方政治家,是非常好的溝通橋樑,他們從知識論上承認中國歷史文化多樣性。”他希望有更多全球南方國家的年輕學者到中國來學習,走出西方中心主義,共同完善中國學研究。
“解決全球性問題需要儒家價值觀”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安樂哲的研究領域是儒家哲學。他曾提出一個觀點:儒家哲學中“成己成物”、“成人”與“成仁”串聯起一個動態的“爲人”過程,並稱此概念爲“human becomings”(成爲人)。這一概念與古希臘哲學中將人視爲既定存在的 “human beings”(作爲人)有根本區別。相較於西方傳統,安樂哲認爲,中國哲學能爲人帶來一些不同的啓發。
安樂哲表示,在古典希臘哲學中,我們生而爲人,無法脫離這一本質身份。而在中國儒家哲學裏,我們生於層層嵌套的家庭敘事脈絡之中,並通過對這些關係的內化與實踐,才得以“成人”。“中國儒家思想所構建的是一種生態。在其中,萬物皆通過與他者的關聯而得以共生共榮,正所謂‘一多不分’。”(‘一’與‘多’互爲依存、渾然一體的關係,強調萬物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編者注)他認爲,“仁”是闡明此理最精微的一個概念,其所代表的並非利他或利己,而是一種深刻的共生成就:鄰人之善即自身之善——“己欲立而立人”。
安樂哲認爲,當今世界需要儒家價值觀:無論作爲個體、集體還是主權國家,我們都是命運與共的整體。“儒家價值觀告訴我們:沒有哪一方能獨自解決全球性問題,同舟共濟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安樂哲稱,這也最終將把人們引向一個理想的優化共生體系。
中國文化對海外的影響還體現在藝術方面。伊朗國家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納思霖在訪談中提到,細密畫在伊朗是最重要的一個文化元素。“中國藝術對細密畫最大的影響要追溯到元朝。”納思霖舉例稱,中國畫家比較喜歡自然元素,在伊朗的細密畫中可以看到自然元素。納思霖表示,“每個地方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這些文明進行了藝術交流”。
“我的中國學之路從羅馬開始”
作爲一名歷史專業出身的學者,國家圖書館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資料中心副主任尹漢超一直從事海外中國問題研究工作。談到“從中國看世界”,尹漢超以自己對“羅馬”的概念說起。“正如我在《國家圖書館與中國學:1909-1949》後記中所寫:直到我初中畢業,‘羅馬’僅僅是停留在書本上抽象的知識點。”而從大學之後,尹漢超對歷史學不再滿足於按時間順序羅列史實、人物,而是致力於一種整體性的理解。“它讓我們學會通過歷史來理解自身,反思當下,並運用這種深遠的眼光,去回應我們此時此刻所關切的、關於過去與現在的種種問題。”
尹漢超表示,從中國看世界,既要看清自身文明的獨特性,也要讀懂其他文明的“文化基因”源自何處,“通俗點講,我們不僅要看清自己腳下走過的路,也要看懂別人走過的路”。
“羅馬在我人生當中的確扮演了學術生命原點的角色。”2007年,尹漢超成功申請到意大利羅馬智慧大學的獎學金,在東方學院,第一次真切地接觸到許多漢學家,如馬西尼、保羅、費琳、馬諾等,他們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更能以中文展開深入的學術對話。“我也參加過他們舉辦的學術會議,這讓我第一次直觀感受到漢學作爲一種跨文化實踐的真實形態。”人們常說“條條大道通羅馬”,而尹漢超的中國學研究之路,或許恰是從羅馬開始。
尹漢超希望,當有一天,源自中國實踐、基於中國範式、又通過國際規範得以清晰表達的理論,能夠真正影響和改變全球對中國乃至對世界本身的認知時,“世界中國學”就將昇華爲一個響亮的“中國學派”,“這正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歷史責任”。
每個漢字都承載歷史文化和審美價值
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法國漢學家白樂桑的新書《漢語—表意文字的王國》封面設計十分獨特,融入了多個漢字元素。對此,白樂桑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大家可能不知道,歷史最悠久的正規中文第二語言教育機構正是誕生在法國”。據他介紹,早在1814年,法國高等學府法蘭西公學院就設立了中文教授職位,而第一任中文教授正是一名法國人,他中文名叫雷穆沙。“直到今天,漢字的獨特性與魅力是很多人選擇學習漢語的重要原因。”
“我本人也不例外。如果沒有漢字,我今天很可能就不會在這裏,也不會主修漢語。”白樂桑談到,漢字的獨特性、詩性和美學價值,對於吸引學習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漢字不僅是記錄語言的工具,更是具有象徵意義和藝術價值的文化符號。”
白樂桑表示,“每一個漢字背後,都包含豐富的學問和文化知識,這使得漢字教學可以獨立成學,而不僅僅是輔助語言的工具”。白樂桑舉例稱,他曾經開設漢字課程,如果按照常規拉丁字母語言教學安排幾個小時就足夠,但漢字課程可以延續一年甚至更久,因爲每一個漢字都承載了歷史、文化和審美價值。“漢字遠遠超越了工具性的價值。”
“從早期法國漢學教育,到參與中文教學、國際課程以及跨學科研究,我見證了漢學和中國學在全球的專業化、系統化發展。”對他而言,漢學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是一種文化橋樑。“通過漢學研究,我們理解中國文化的深度與美學價值,也讓世界看到中國學術與文化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