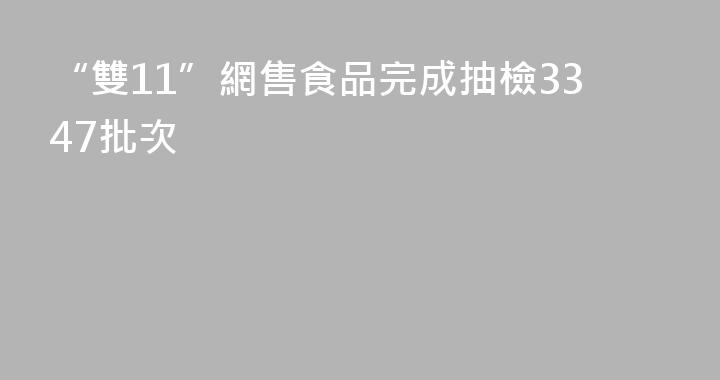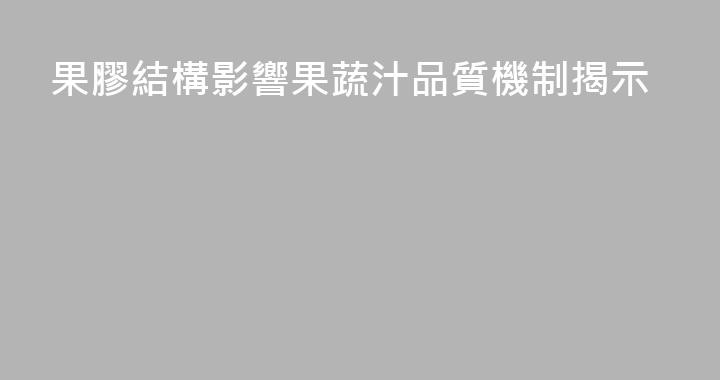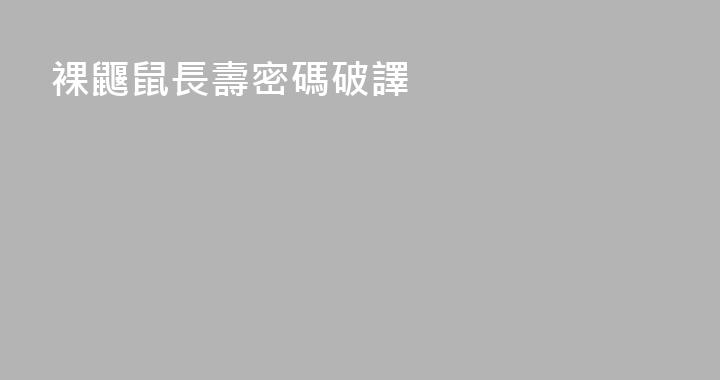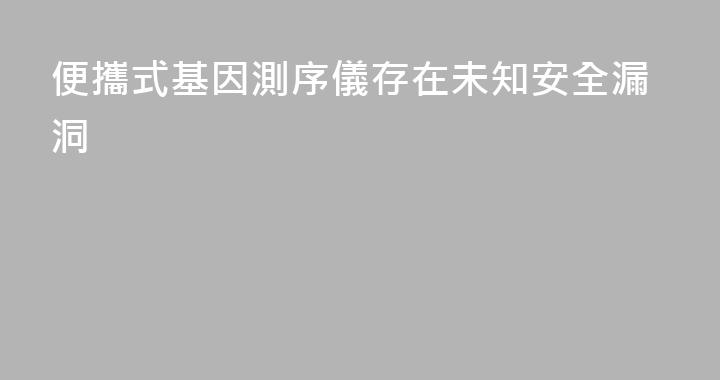□ 本報見習記者 丁一
□ 本報記者 陳磊
“我活到108歲,試茶80多年了……”被譽爲我國茶學界泰斗、20世紀十大茶人的張天福近日突然“出現”在公衆視野,爲某茶企代言。
這段出自人工智能之手的商業廣告視頻引發社會熱議。因爲視頻中的張天福已於2017年6月逝世,享年108歲。
利用逝者生前的照片、視頻、文字記錄等歷史數據,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數字化模擬等手段再現已故人物的聲音、影像、行爲等,被稱爲“數字復活”。近年來,多位知名逝者被數字復活後引發爭議和廣泛關注。
受訪專家認爲,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式發展,降低了數字復活的技術門檻和成本,讓數字復活逝者變得越來越簡單,進而對現有法律秩序和倫理觀念提出了挑戰。
專家建議,爲應對這種挑戰,可考慮構建一個以私法爲基礎、公法爲保障、多方協同治理爲路徑的系統性框架,以規制數字復活。在私法層面,細化數字遺產中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的繼承和行使規則,可探索建立生前預囑或授權制度;在公法層面,監管重心應從末端內容審查,向前端的技術源頭和關鍵平臺延伸。
數字復活引發爭議
逝者被數字復活並引發熱議的事例近年來時有發生。
去年,有網友用AI技術“復活”李玟、喬任梁等已逝明星,在視頻評論區,有人打着溫情的名義,趁機做起AI推廣、收費服務……
對於這樣的行爲,相關方多感到不適。比如喬任梁的父親公開表示不能接受,希望這類視頻儘快下架;李玟的母親公開發布了一則律師聲明,要求下架刪除“AI復活李玟”系列短視頻。
但《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也有親屬主動利用AI技術復活逝者。音樂人包小柏的女兒去世後,他十分思念,就利用AI技術讓女兒在數字世界“復活”。“她”不僅可以唱歌,還能與人對話。
“數字復活的本質,是對‘逝者人格標識’的新形態使用,具有滿足人情倫理、豐富數字身後事等多方面價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琦介紹說,根據生成數字人智能化程度的不同,數字復活可以分爲幾個層次:最簡單的數字復活,是利用AI使逝者照片“動起來”,使逝者數字人能夠做出簡單表情或者動作;稍高層次的數字復活,是具備任意交流功能的數字人,可以與他人進行對話;更高層次的數字復活,是具有學習能力的數字人,可以不斷從真人的網絡活動中學習,在真人去世後持續與親友交流。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主任陳天昊認爲,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獲得突破式發展,尤其是其成本降低和易用性提升後,數字復活行爲大量出現,對現有倫理觀念提出了挑戰,也呼喚法律秩序的介入與應對。
“技術能力的普及化和平權化,使得有可能實施數字復活的行爲主體範圍大大擴展,從而改變了數字復活治理的難度與模式。”他說。
相關規則有待細化
近年來,數字復活引發爭議不斷,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此是否可以有效應對?
陳天昊介紹說,我國目前已初步形成由法律與專項行政規範性文件構成的數字技術規制體系。在法律層面,民法典人格權編系統性地規定了對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譽、隱私等權利的保護,並專門確立了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規則,且該權利旨在保護逝者尊嚴而非賦予近親屬任意處分權。在專項行政規範性文件層面,《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明確了對生成內容進行顯著標識和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責任等重要制度。
在他看來,現行法律及相關規範在適應技術發展方面仍存在問題:一是規則的細化程度尚顯不足,比如對於非商業性使用、家庭內部緬懷等場景的行爲邊界缺乏具體規定;二是執行機制面臨挑戰,現有監管措施對大型平臺較爲有效,但對於數量龐大、分佈分散的個人及小型開發者,尚缺乏足夠有效的監管工具。
王琦認爲,數字復活的法律規制還涉及不同法律法規之間的協作問題,需要理出清晰的規制線索,使法律法規能夠被精確適用。例如,對於其他人是否有權決定對逝者數字復活的問題,雖然當前並沒有直接對其作出規定,但是可以從司法實踐中關於逝者遺體、骨灰處置的相關規定中尋找答案。
“正如逝者的普通親友或者熟人一般無權決定逝者的遺體安置一樣,粉絲往往無權決定明星的數字復活。而且生成數字人對已公開個人信息的使用已經遠遠超出了合理的範圍,具有高於原始信息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說,粉絲也無權利用已公開的個人信息對明星進行數字復活。”他介紹說。
建立清晰價值位階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已經是客觀事實,基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數字復活技術也將愈加成熟,相關規定該如何完善以協調各方利益主體?
在陳天昊看來,可以考慮構建一個以私法爲基礎、公法爲保障、多方協同治理爲路徑的系統性框架,規制數字復活。制度設計的核心基石是維護人格尊嚴,所有規則均不得與之相牴觸,對於侵權行爲,應同時賦予近親屬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和行政機關主動介入的權力。
具體而言,他認爲,在私法層面,需要細化數字遺產中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的繼承和行使規則,可探索建立生前預囑或授權制度,並在逝者未選擇該制度安排時,對商業性使用數字復活設定近親屬一致同意等嚴格條件。在公法及治理層面,監管重心應從末端內容審查向前端的技術源頭和關鍵平臺延伸,即對基礎模型開發者提出更強的安全與倫理責任要求,特別是在模型的後訓練階段進行專門的價值對齊,並且要壓實內容分發平臺的審覈義務,不斷提升其對相關投訴的處置效率。
受訪專家認爲,在進行制度設計時,首先需要明確數字復活由誰發起。爲此,應精確識別與平衡其中牽涉的多元利益主體。這些主體包括逝者本人、其近親屬、技術使用者、平臺方以及社會公衆。在協調各方利益時,必須建立清晰的價值位階。
在王琦看來,應優先尊重本人意願。數字人能否進行商業性使用,只能由本人生前作出安排。本人還可以在生前明確,禁止他人對自己進行數字復活。
“逝者近親屬對逝者的追思紀念是人類的普遍情感需求,是正當利益,應當被肯定。但近親屬對數字人的使用僅限於追思紀念的範圍內,不應超出追思目的,尤其是不能對數字人進行商業性使用和將具有交流能力的數字人接口公開。並且發起主體僅限於逝者近親屬,其他親友不能進行數字復活。”王琦說。
他進一步分析,出於公共利益,可以基於人格權合理使用制度進行數字復活。這主要適用的場合是數字文博、知識文化傳承、教育科研活動等,數字人在這些活動中具有超出通常媒介的獨特價值,其所呈現出來的效果是簡單的照片和視頻所無法比擬的,需要強調的是,這種使用必須在極其審慎的考量和嚴格的程序下進行,如果簡單的人格標識(照片、視頻等)就能滿足公共利益,就沒有必要利用最複雜、風險最大的數字人。此外,逝者的人格尊嚴是不可減損的絕對性法益,任何可能被視爲貶損、醜化或不尊重逝者的行爲都應被嚴格禁止。
“還應積極與技術社羣開展合作,從而推動行業自律和技術自律;鼓勵研發能夠識別和追溯侵權內容的技術工具,形成能夠有效約束彌散化行爲主體的、開放協同的治理體系,從而在劃定法律底線、疏導合理訴求的同時,引導技術朝着尊重個體、服務社會的方向發展。”陳天昊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