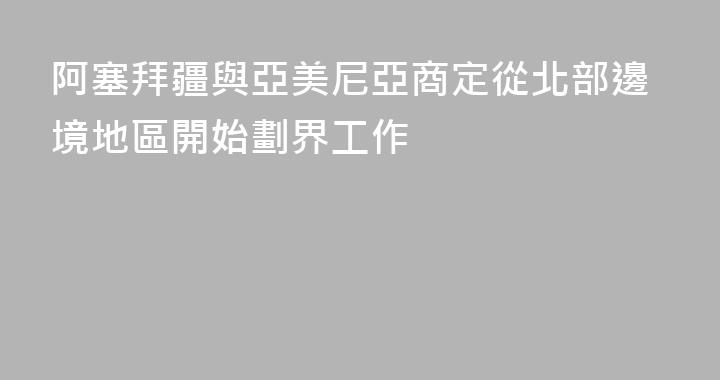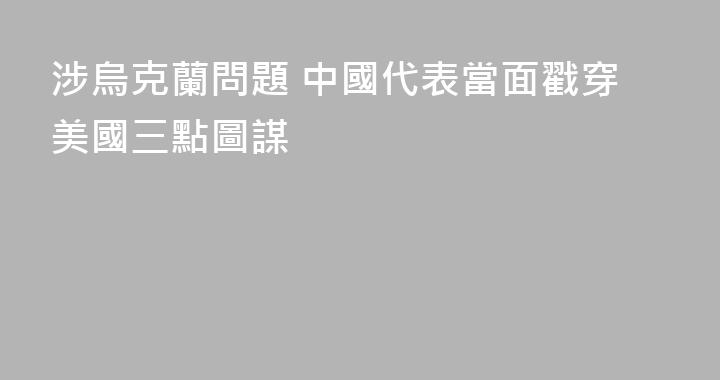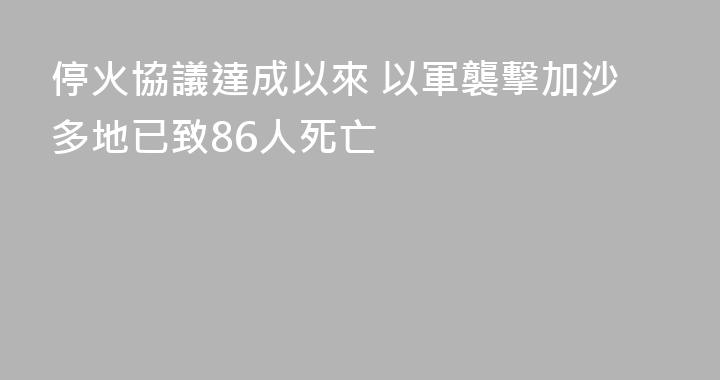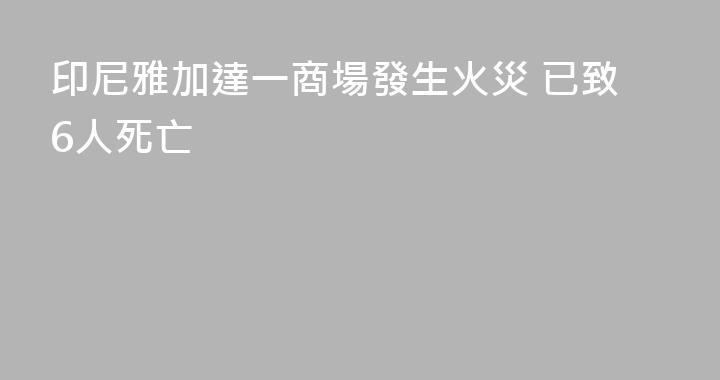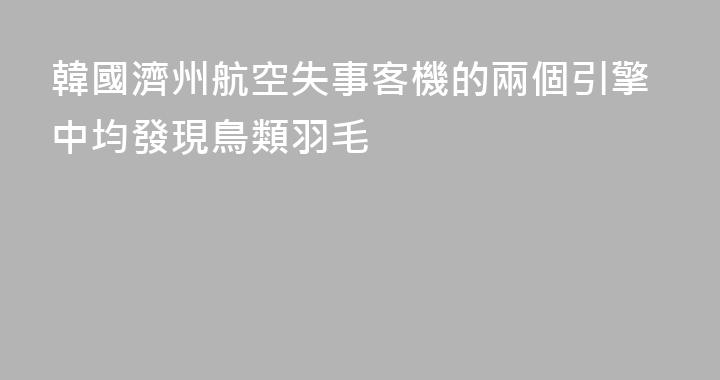西班牙《國家報》1月11日文章,原題:文學界的愛國者與無根者 集體身份的法則嚴苛,一些作家即使長期生活在某地甚至出生於此,也難逃被視作外來者的命運。然而,不公、仇外和謊言的盛行正促使人們重新找回應有的價值觀:公民自由與權利、社會正義以及人人平等。人們開始放下對出身的執着,更加捍衛自由意志與自願的團結,而非受限於虛構特徵所帶來的羣體認同和受害者情結。
身份製造者擅長制定規則,劃分誰是自己人,誰應被接納或驅逐,誰是敵人、叛徒、異端。例如,儘管弗朗茨·卡夫卡出生並終老於布拉格,他仍難以被視爲捷克作家。他的“錯誤”在於擁有兩種母語,且以德語創作,更別提他的猶太身份。在布拉格,卡夫卡更多隻是個旅遊景點象徵。他一邊被認定爲外國人,一邊又被利用獲利,就如同極端民族主義者一邊煽動對移民的恐懼,一邊又利用他們的無助牟利。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在都柏林未獲好評,直至去世後,愛爾蘭才意識到他的巨大文化貢獻,並將其文學遺產轉化爲商業利益。
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是西班牙文學中極具世界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與馬德里、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城市都有着深厚聯繫,但靈魂深處仍屬於格拉納達。傳記作家伊恩·吉布森曾在格拉納達尋找洛爾迦的蹤跡,卻發現整個城市對洛爾迦都保持沉默和冷漠的態度。
就如喬伊斯之於都柏林、卡夫卡之於布拉格、洛爾迦之於格拉納達,敖德薩也無法與伊薩克·巴別爾分割。巴別爾在《敖德薩故事集》中秉承了莫泊桑與契訶夫的傳統,又融入了底層社會特有的滑稽幽默,以猶太小男孩的視角,觀察那座混亂、喧囂、充滿生機的城市——敖德薩。俄烏衝突後,烏克蘭掀起抵制俄羅斯文化的浪潮,甚至擴展至對俄語文化的抹殺。但這終究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民族純潔”的妄想。巴別爾的“原罪”,只不過是用俄語創作文學。他在烏克蘭語、意第緒語和俄語環境中成長,並用俄語創作出讓敖德薩成爲文學之都的故事,那些極端主義者或許能推倒他的雕像,但無法抹去他筆下那個屬於每一位讀者的敖德薩。“人爲製造身份認同”的羣體夢想着用一種根除手術實現目的,而其所能得到的最多隻是殘酷的肢解之痛。(作者安東尼奧·穆尼奧斯·莫利納,馮子謙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