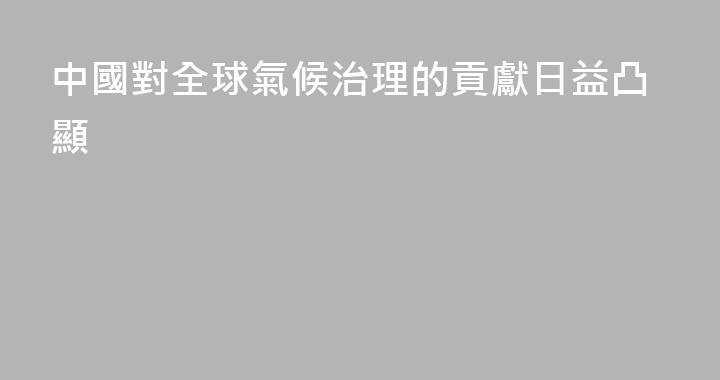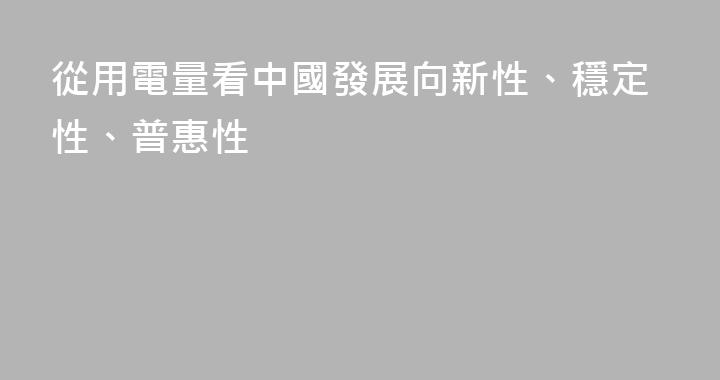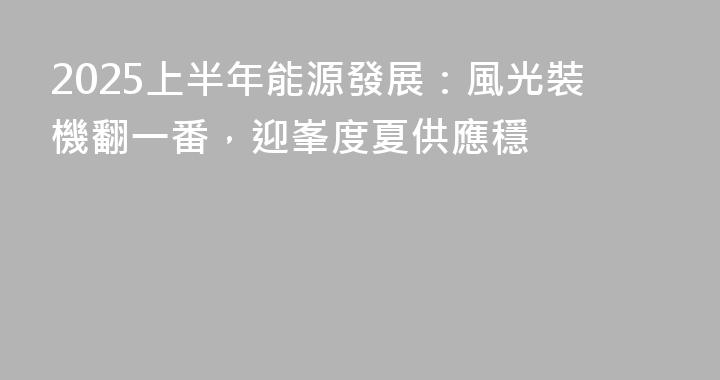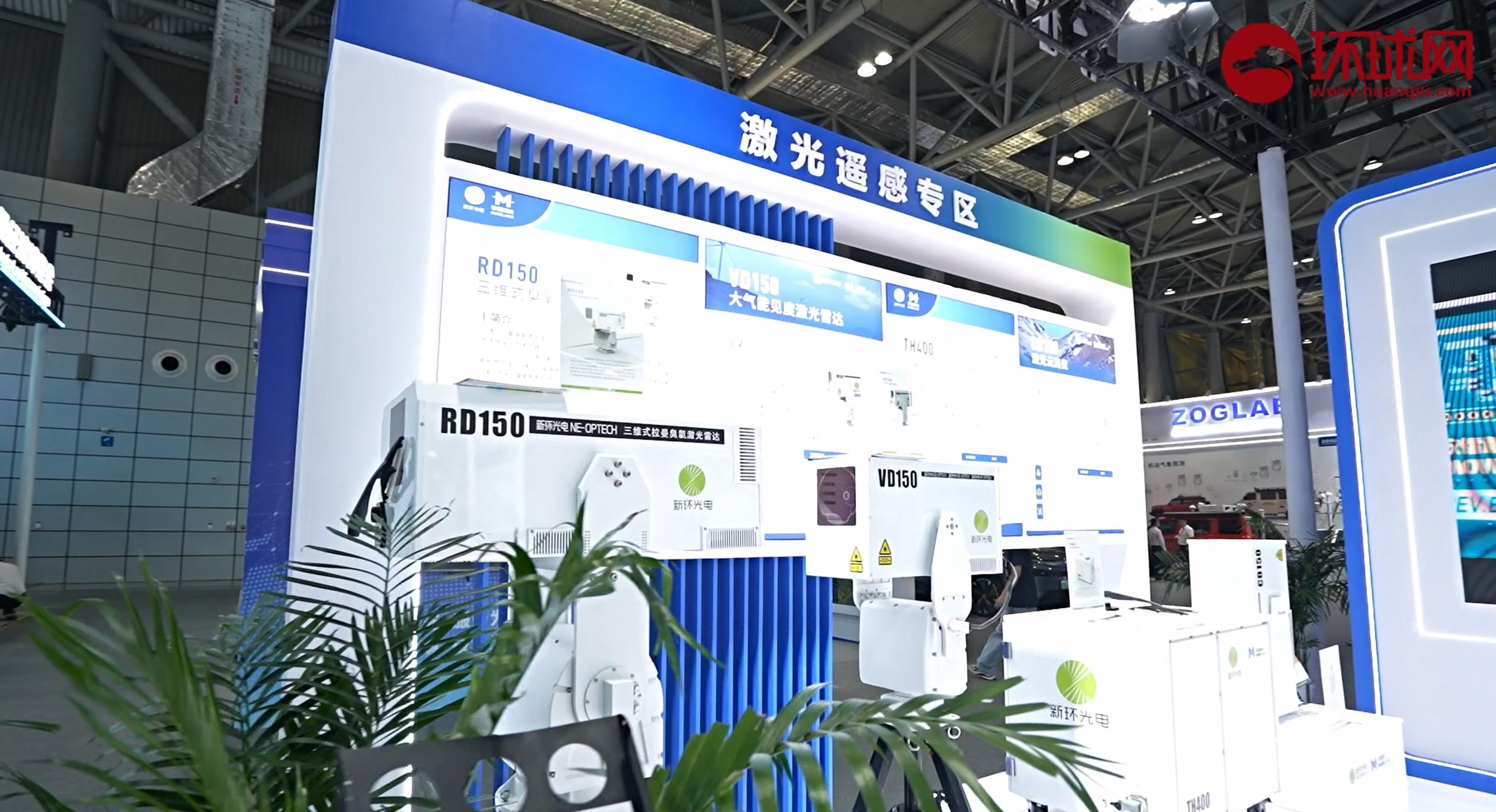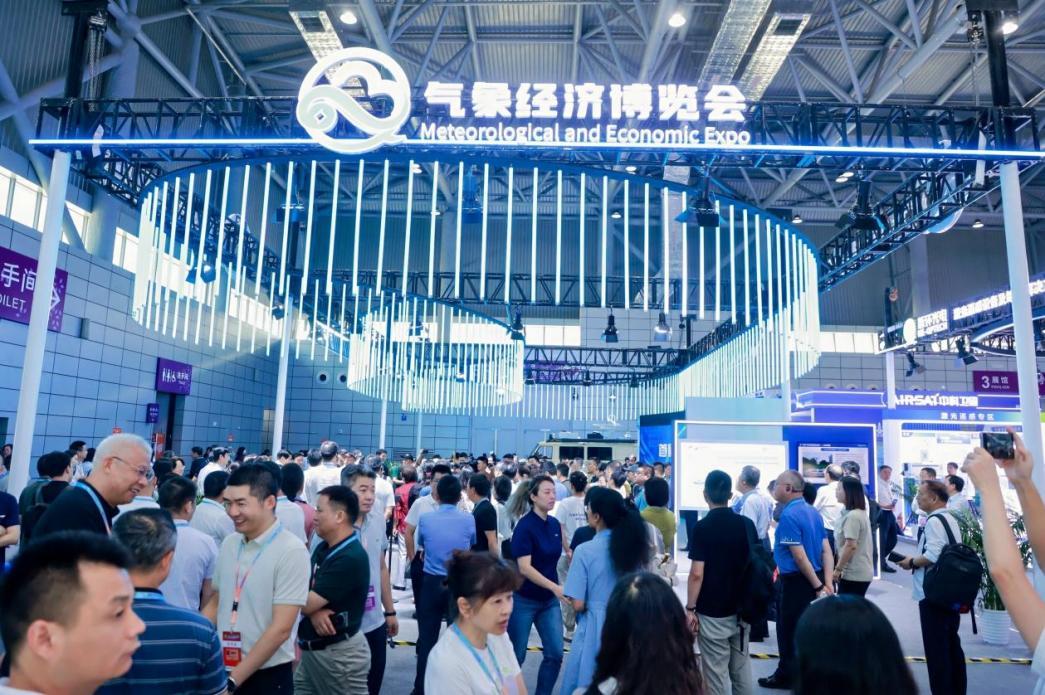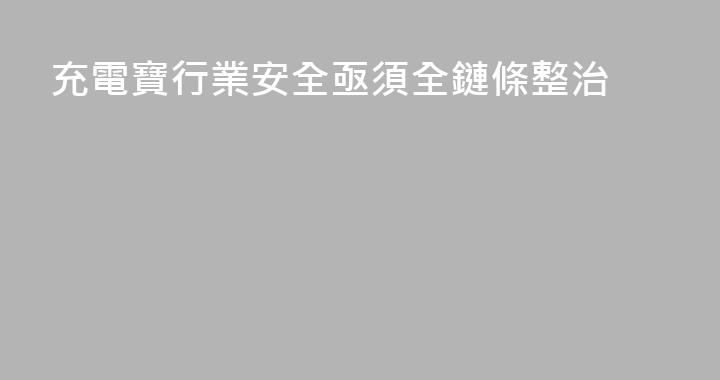◆本報記者童克難
外排滲濾液COD濃度超標53.2倍,污水處理設施3年來有一半以上時間停運,調節池高位積存滲濾液存在嚴重風險隱患……近日,雲南省西雙版納州景洪市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場因環境問題突出,被督察組“點名批評”。
記者通過採訪督察人員及梳理公開信息發現,治污設施淪爲“污染源”背後的根本原因,是企業主體責任、部門監管責任以及政府法律責任的不落實。
國有企業漠視法律法規,運營10年後才建成滲濾液處理設施
資料顯示,此次被“點名”的垃圾處理場由景洪市城市管理局下屬環衛清潔有限責任公司管理運行。這家公司的主要經營範圍爲生活垃圾處置服務等。
從典型案例通報的情況來看,作爲一家國有企業,景洪市環衛清潔有限責任公司非但不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反而使垃圾處理場長期存在違法行爲,導致環境受到污染,其根本原因是對相關法律法規的漠視。
“我行我素”,是典型案例中定義這家企業和垃圾處理場面對生態環境部門處罰時的態度。
督察發現,這家垃圾處理場的滲濾液處理站在線監控設施自2019年12月安裝以來一直處於閒置狀態。即便在今年3月西雙版納州生態環境局檢查發現這一問題並立案查處的情況下,其依然我行我素,不予整改。
直至今年4月7日督察組進行現場督察時,垃圾處理場才委託設備方對設備進行調試。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其任由在線監控設施閒置。
“我行我素”,還體現在這家企業在建設過程中違反環評的“三同時”要求。
按照景洪市環衛清潔有限責任公司法人趙江華的介紹,垃圾處理場於2004年建成使用。“2014年,爲保證垃圾滲濾液有效處理,項目新增處理能力爲130噸/日的垃圾滲濾液處置設施。”
“也就是說,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裏,這家垃圾處理場的滲濾液沒有經過處理設施的處理。”督察人員表示。
現場的情況,也能佐證這個說法。
今年1月,生態環境部西南督察局對這家企業進行現場排查時發現,垃圾處理場部分滲濾液通過填埋區底部防滲膜下的地下水導流渠直接外排。外排滲濾液COD濃度爲5420mg/L、氨氮濃度爲132mg/L,分別超過《生活垃圾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GB16889-2008)表2限值的53.2倍和4.3倍。
“導流渠的廢水通過雨水溝排入瀾滄江的支流菜陽河。導流渠底部呈黑色,是長期排放超標廢水導致的。”督察人員說。
監管部門不作爲,治污設施長期停運
分析梳理監管部門的責任落實情況,先從2014年5月的一份環評報告說起。
在公開的《景洪市垃圾處理場擴建工程垃圾處理設施政府信息公開本環評報告》(以下簡稱《環評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景洪市垃圾處理場採用回噴‘自然蒸發法’處理滲濾液,因爲處理方式不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GB16889-2008)的要求,景洪市環衛清潔有限責任公司擬實施垃圾處理場擴建項目,包括C庫區的防滲處理工程和垃圾滲濾液處理工程。”
由此可以判斷出,企業及相關部門清楚地知道,2008年之後所謂回噴“自然蒸發法”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
再說“肉眼可及”的現場情況。
督察組在現場檢查時發現,這家垃圾處理場每一層已經閉庫、覆膜、覆土的作業面區域表層幾乎都有滲濾液冒出,場區內“污水橫流”。設計容積爲3.5萬立方米的調節池,目前積存約3萬立方米未處理的滲濾液。
“按照要求,填埋場的滲濾液應該做到‘日產日清’,正常情況下不應該有積存。”督察人員表示。
督察人員現場檢查時還發現,2018年以來,這家垃圾處理場多次、長時間停運滲濾液處理設施。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至2020年,3年分別停運231天、172天、160天,佔比高達50%以上。
對於停運後滲濾液的處理,企業相關人員表示仍採用“回噴”的處理方法。即便如此,其記錄也是漏洞百出。
調閱滲濾液產生量、處理量和回噴記錄,督察人員發現,企業提供的3位“記錄人”的筆跡高度相似。對此,當地公安部門對記錄中3人筆跡的鑑定結果是:其中兩人姓名傾向爲同一人筆跡。
如此明顯的種種問題,監管部門是否發現?
景洪市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場於2004年建成,其主管單位分別爲2019年3月前的景洪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之後的景洪市城市管理局。
景洪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李建輝表示,該局多次對垃圾填埋場進行檢查,其結果是“該填埋場運行基本正常。”
對垃圾填埋場的現場檢查,景洪市城市管理局局長高嵩也表示:“主要是對相關員工履職情況進行檢查。”“ 但由於環境保護專業知識掌握不多,其他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更多的是直觀檢查,如填埋區堆存是否規範、滲濾液處理站出水是否清澈等。”
“基本正常”和“規範”“清澈”等描述,顯然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由此可見,企業存在的長期違法行爲,與主管部門敷衍應付、不嚴不實的工作作風有直接關係。
地方政府慢作爲,上級補助“打水漂”
3年時間,滲濾液處理設施停運高達563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255.61萬元投資。
《環評報告》顯示,此滲濾液處理設施當年估算的工程費用爲1255.61萬元,資金籌措主要由國家補助、地方政府及自籌資金(含銀行貸款)3部分組成。
拋開企業自籌部分,治污設施3年來停運時間達50%以上,說明國家補助及地方政府的資金沒能真正發揮作用。
與之相對應的,是垃圾處理場的“照常收費”。據瞭解,這家企業的主要運行費用來自向市民徵收垃圾處理費。以2019年爲例,徵收費用約2000萬元。
典型案例中的另一個信息,也值得注意。“2018年、2019年,景洪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城市管理局分別就垃圾處理場滲濾液環境風險隱患突出的問題向景洪市政府進行了書面彙報。”
高嵩表示,市政府領導“也非常重視。”
但督察發現,在收到相關部門的書面彙報之後,景洪市政府既未研究部署,也不督促解決,任由垃圾處理場各類環境問題持續存在。
在典型案例中,督察組對景洪市政府的評價是“景洪市政府對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置工作推動不力。”
其另一個表現,是對城市配套環保設施統籌建設不力,慢作爲甚至不作爲明顯。
從督察組掌握的情況來看,目前這家垃圾處理場滲濾液的產生量爲每天150立方米左右,大於其每天130立方米的處理能力,即便正常運行也已經不能滿足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要求。
爲解決問題,景洪市自2016年就考慮用垃圾焚燒發電代替衛生填埋。但直至2020年,項目才完成徵地,目前還處於場地平整階段。
有關法律明確,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統籌城鄉建設污水處理設施及配套管網,固體廢物的收集、運輸和處置等環境衛生設施,危險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場所以及其他環境保護公共設施,並保障其正常運行。
由此可見,景洪市政府並沒有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是違法行爲長期存在、污染問題久拖不決,以及新建替代項目進展緩慢的根本原因。
市政府領導“也非常重視”更是無從談起。
景洪市能否知恥後勇,切實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督察組將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