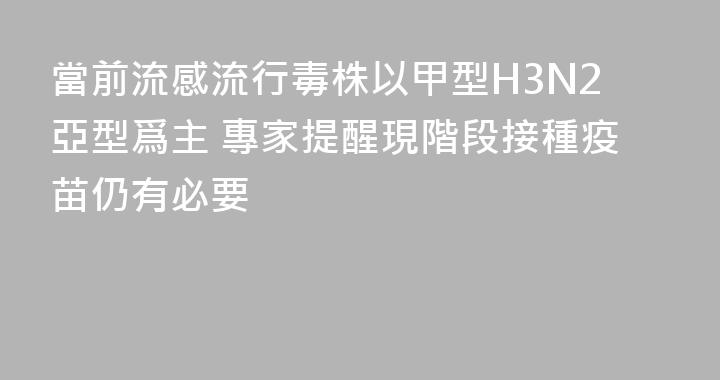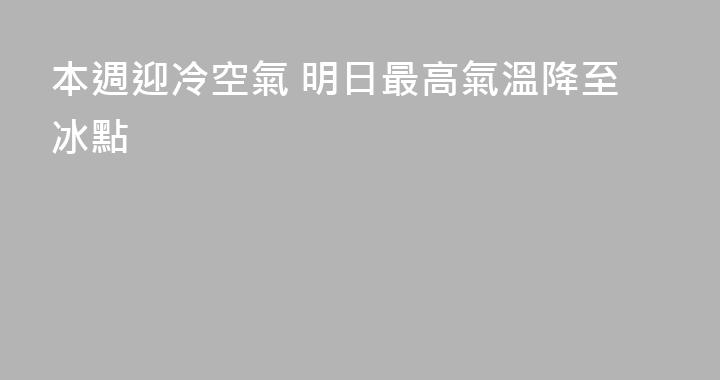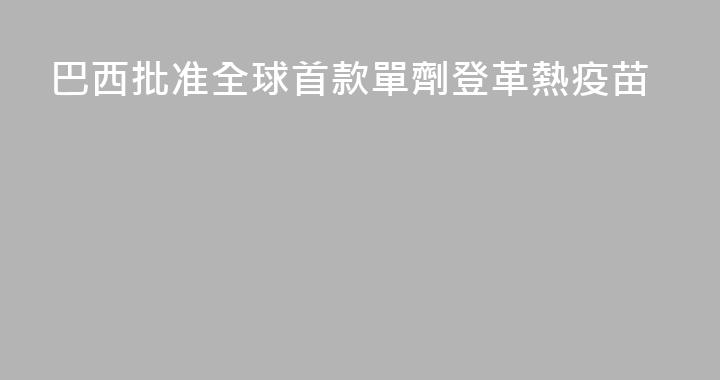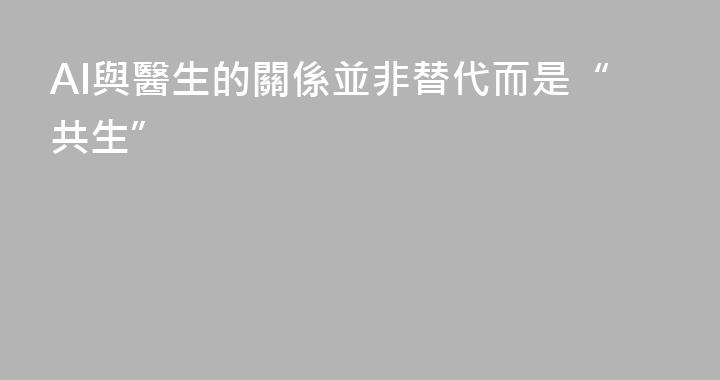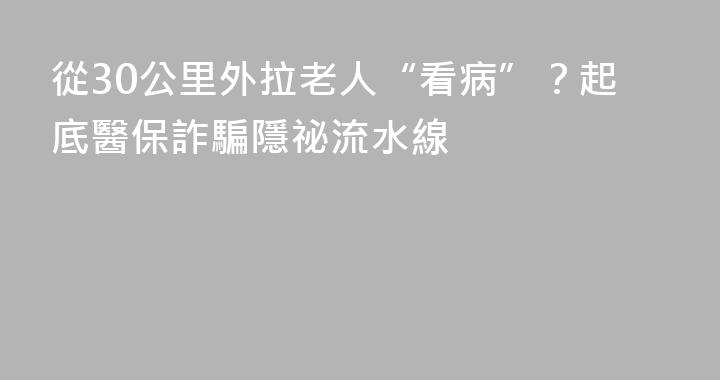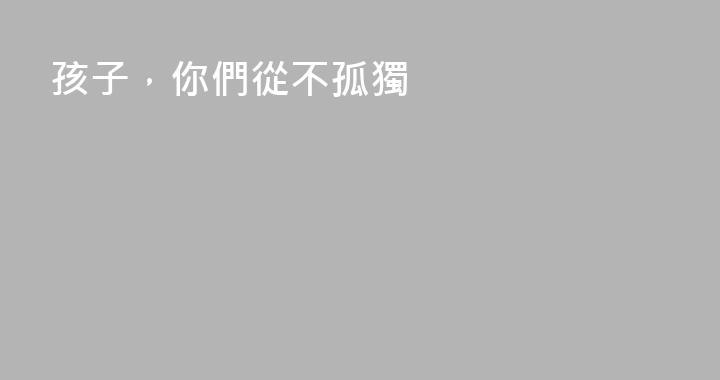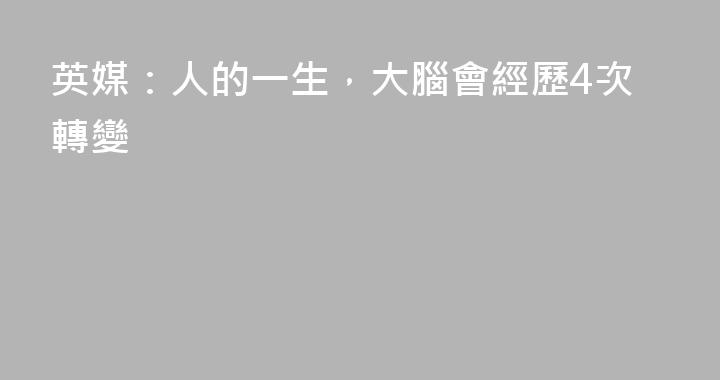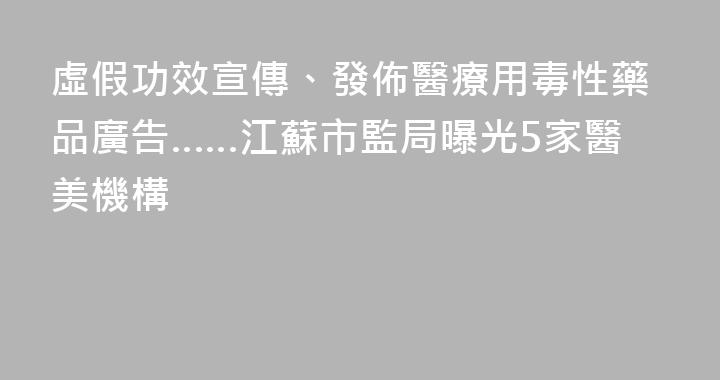隨着我國老齡化程度加深和老人就醫需求增長,陪診服務作爲醫療體系的重要補充,亟須儘快走上規範化、專業化發展之路。如何構建規範的陪診服務體系,讓“老有所醫”更具溫度與質量,成爲普遍關注的議題。
在老齡化程度高、三甲醫院集聚的上海,市場需求催生了“陪診師”這一新行業。希望提供陪診服務的,有子女不在身邊或無子女的老年人,有“搞不定”認知症患者的家屬,有需要定期複查的慢性病患者,有獨自去醫院檢查的孕婦,還有從外地來上海就醫的患者和家屬等。
在不少醫院門口,可以見到打着廣告、明碼標價幾十元一小時陪診的個體從業者;在各類養老服務機構、第三方平臺,可以約到代配藥、陪同就醫等服務。據悉,“陪診師”尚未納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的《職業分類大典》,行業內存在職業認可度不高、服務質量良莠不齊、收費價格混亂等問題。
今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聯合市衛生健康委等部門印發《上海市老年人助醫陪診服務試點方案》,在前期小範圍試點的基礎上,明確在浦東、楊浦、松江等9個區進一步試點,目標是發展一批規範提供陪診服務的養老服務機構和陪診師隊伍,探索形成老年人助醫陪診服務流程、收費機制和監管舉措,總結提煉相關工作規範標準,推動上海市老年人陪診服務規範發展。
陪診師相當於患者的“臨時兒女”
85後陪診師付蓉是上海市長寧區一家養老服務公司的員工,這家公司與當地政府合作,爲所在街鎮提供陪診、代配藥、術後健康陪護、保潔等爲老服務。
付蓉形容說,陪診師相當於患者的“臨時兒女”,需要熟悉就醫流程、提前掌握患者的各項信息,還要有耐心、善於溝通,提供“情緒價值”。通常來說,陪診師接單後,要提前幫助患者準備好病歷、檢查報告,確認好掛號等流程;就醫當天,要選擇合適的時間到醫院候診,或上門接患者到醫院;到醫院後,陪診師全程陪同患者候診、簽到、看診,記錄病情和醫囑,做好檢查、取藥等;就醫完成後,要將所有信息整理好並告知患者或家屬。
“雖然現在做陪診師沒有門檻,但其實挺辛苦的,而且有一定技術含量。”付蓉告訴記者,她從酒店管理專業畢業後,在酒店做過服務生、領班,後來從事過幾年房產銷售,積累了一定的銷售技巧和溝通能力。六七年前,付蓉偶然在醫院接觸到陪診服務,並在朋友的介紹下嘗試“接單”。
當時,付蓉接待了從溫州來上海複查病情的一對老夫妻,陪同他們掛號、付費、看診,記錄了醫生給出的方案和建議。就醫結束後,她把客戶送到高鐵站,並將就診情況詳細告知老人子女。“因爲是第一次接單,我全程都特別專注、小心,雖然只收到100多元報酬,但我覺得這是個不錯的行業,可以做全職。”付蓉說。
近3年來,付蓉從兼職轉爲全職從事陪診工作,接待過上百位客戶。去年4月,她通過公司報名,參加了上海開放大學的陪診師培訓班,通過筆試與實操考試,拿到由上海開放大學和上海市養老服務行業協會共同頒發的“陪診師”證。
付蓉觀察到,目前從事陪診行業的,多數是40歲以上的家政服務員、退休護士、經過短暫培訓的平臺簽約服務人員,以兼職爲主。她說:“比起有醫療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士,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優勢,所以在工作中會主動學習,積累經驗。比如儘量提前全面瞭解患者的病情和發病原因,更好地告知醫生;患者沒有聽清楚的醫囑、注意不到的細節,我都會加以提醒,比如做胃腸鏡該不該選無痛的,到醫院要帶哪些預約單、檢查單,做檢查前幾小時要禁食禁水等,儘可能全面告訴患者。”
陪診是一種“剛需”,但職業認可度不高
在社交媒體上,圍繞“陪診”同時存在多種聲音:想入行做陪診師的年輕人,被所謂“月薪過萬”的信息所吸引,但嘗試後遇到接單不穩定、客戶難溝通、收入無法保證等問題,還有人向所謂培訓機構繳納了幾千元費用,卻沒有學到相應的知識、技能;而一些有陪診需求的消費者,又無法理解“陪看一次病要兩三百元”的價格。
在付蓉看來,之所以存在這種矛盾,是陪診市場供需不匹配導致:“陪診師這個職業還沒有被納入正式的新職業體系,職業認可度不高,缺乏統一的培訓和技能標準,從事陪診的很多是兼職的非專業人員,或者只是短暫嘗試一下,發現收入不穩定、又沒有社會保障就不做了,總體上服務質量參差不齊。”
90後張峻彥2016年進入養老服務行業,從事過多個管理崗位,曾針對上海陪診市場需求做過調研。她認爲,陪診的確是一種“剛需”,但陪診師的職業知曉度、陪診的市場成熟度不高,消費者還沒有形成比較強的付費觀念。
張峻彥告訴記者,目前上海的陪診需求主要通過線下個人接單、線上服務平臺派單和養老服務機構內部服務3種方式解決。“在線下接單的,一般是在醫院門口的自行車上貼個廣告,以個人或夫妻小團隊方式提供服務;線上平臺很少有專注做陪診的,往往同時提供多種服務,爲兼職人員和消費者提供平臺;此外在養老院、街道爲老服務中心等機構,由院內護理師提供收費服務。”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發現,目前在養老服務機構內部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陪診機制,一般由養老護理員兼任陪診師,外出服務費用以單獨支付或計算進工資的方式發給護理員。
上海市松江區的醫養融合大型養老社區“泰康之家·申園”護理總監朱虹告訴記者,院內老人對陪診助醫的需求比較多。由於醫院內人多、就醫流程長,患者需要在多個地方往返掛號、付費等,看一次病會花費較長時間,行動不便、體力不支的老人,需要有人陪同以提供必要的行動輔助。有老人在就醫過程中可能會產生一些低落情緒,有陪診人員在身邊,可以進行安撫,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朱虹說,安排園區內有豐富養老護理經驗、善於與老人溝通的護理師陪診,可以增加老人的信任度和安全感。在老人如廁、輪椅轉移等過程中,護理師可以提供生活照護服務。護理師通常具有一定的醫療護理知識及應急處置能力,如果老人出現緊急情況,可以提供有效措施,讓老人就醫時安心,也讓家屬更放心。
待陪診市場更趨成熟,會吸納更多從業者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注意到,針對陪診師缺乏統一培訓和技能標準、市場上陪診服務良莠不齊、標價混亂等問題,《上海市老年人助醫陪診服務試點方案》給出具體的試點措施,包括細化陪診服務內容、發展專業陪診隊伍、建立服務主體名錄、形成合理收費機制、探索對特殊困難老年人的保障機制、建立風險防範機制等。
方案將陪診師明確定義爲“經過一定時長的培訓,運用基本健康衛生和護理知識等相關技能,陪同並協助老年患者接受醫療診治的人員”,試點的範圍包括收住老年人的養老機構、長者照護之家,和具有一定數量陪診師、具備常態化專業服務能力的專業性日託、居家養老服務組織等。
在技能培訓方面,方案提出發展專業陪診隊伍,由試點區民政局根據市民政局統一安排,在相關行業組織支持下,組織培訓機構、大專院校等開展陪診師培訓以及考覈;積極發動養老服務機構的護理員、內設醫療機構護士,以及老齡專業社工、養老顧問等養老服務從業人員參與培訓。
上海開放大學於2023年9月起推出陪診師公益培訓項目,目前已分批次舉辦10餘期培訓班,培訓學員1527人。
上海開放大學非學歷教育部副部長應一告訴記者,這個培訓班的對象主要是上海市社區或養老服務機構內從事護理、社工、醫療等崗位的從業人員,還有少部分來自該校養老、社工相關專業的學生;培訓師資有在老年護理學、醫學、社會工作等領域擁有深厚學術背景的高校教師,長期致力於陪診服務的資深“實戰派”講師,以及三甲醫院主任醫師及護理骨幹。
應一也介紹,每期陪診師培訓4到5天,包括理論課與實訓課。理論課有陪診服務基本流程、醫療就診基本流程、老年人生理心理特點、陪診服務溝通技巧、陪診服務法律責任等;實訓教學包括陪診的全流程實操演練及生命體徵觀察、基礎急救等技能操作。參訓學員經理論考試和實訓操作合格後,方能獲得結業證書。
參加了培訓班的賈林飛曾是一名企業高管,瞭解到陪診師這一行業後,她於去年7月開設了一家小型陪診機構,連她在內共有4名陪診師。她告訴記者:“公司主要面向外地來滬就醫人員提供服務,就醫流程描述清晰,各項服務明碼標價;消費者可以在浦東新區養老服務平臺‘浦老惠’App等渠道下單。”
受訪的業內人士認爲,試點文件的出臺對於行業規範發展、市場知曉度和成熟度提升都會起到促進作用。
在朱虹看來,未來陪診助醫服務會進一步專業化,這意味着養老機構能夠提供更專業、細緻的醫療服務,能夠滿足老年人對高質量醫療服務的需求,從而提升養老機構的整體服務水平,增強市場競爭力,進而促進養老機構的規模擴大和業務拓展,推動整個養老行業的發展和進步。
張峻彥認爲,上海的養老形式多元,今後無論是在養老服務機構居住的老人,還是居家養老的老人,都可以在院內或社區找到專業的陪診師。待陪診市場達到一定成熟度、行業規範建立起來的時候,會吸納更多從業者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