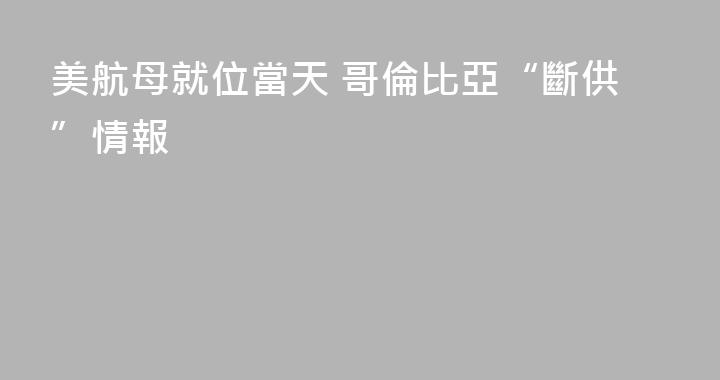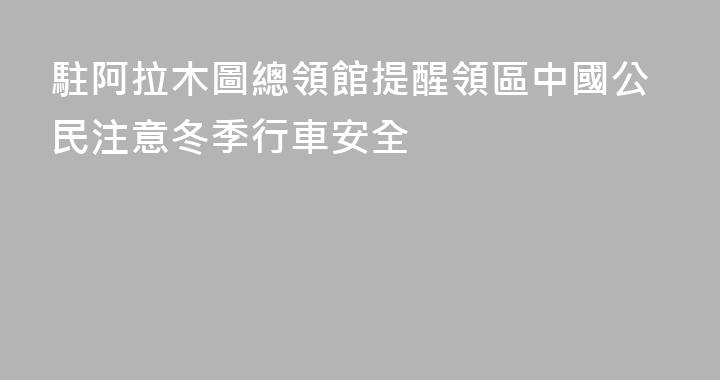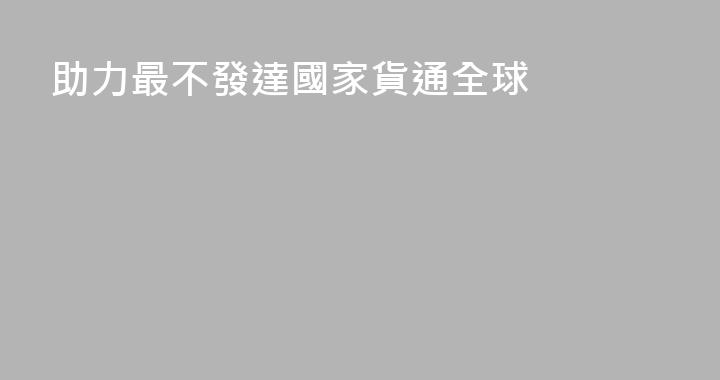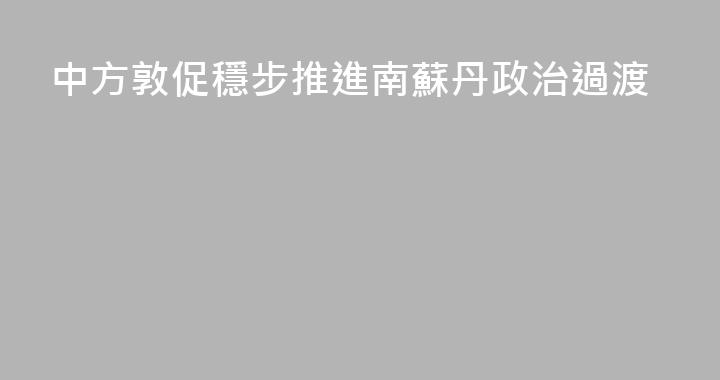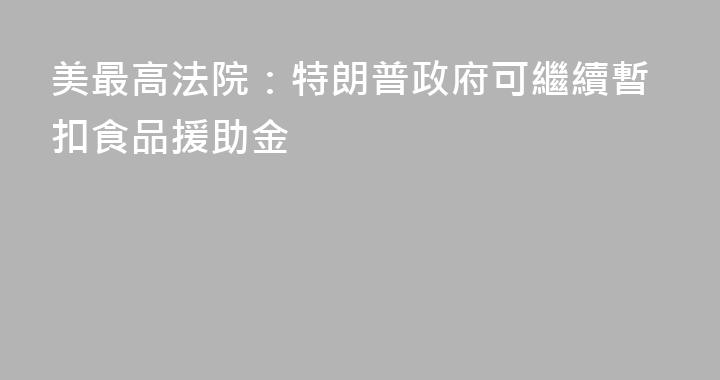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正在巴西貝倫舉行,世界各國政要和科學家與社會團體齊聚一堂,聚焦三大核心議題:推動各國減排承諾更新、推出“全球適應目標(GGA)指標體系”、細化氣候融資機制,共商應對氣候變化大計。
與氣候相關的新聞事件近日也接連登上熱搜,“地球正逼近首個危險的氣候臨界點”“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創歷史新高”等引發關注。那麼,這些變化會給全球氣候和人們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如何理解目前關於氣候變化的爭議?我們請國家氣候中心研究員周兵來說一說。
氣候臨界點是否觸發從何得知?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全球系統研究所近日牽頭髮布由23個國家87個機構的160名科學家共同撰寫的《2025年全球臨界點報告》,明確指出全球熱帶珊瑚礁已突破1.2℃的熱耐受臨界值,正越過生存臨界點。 與此同時,世界氣象組織也發佈了2024年度《溫室氣體公報》,揭示當前大氣中二氧化碳水平創歷史新高,加劇了地球面臨的不斷暖化問題。
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對“氣候臨界點”(Climate tipping points)有明確定義:就氣候系統來說,臨界點指的是全球或區域氣候從一種穩定狀態到另外一種穩定狀態的關鍵門檻。氣候臨界點可通俗理解爲:地球氣候系統中氣候指標達到某個關鍵閾值區間。當氣候指標接近閾值區的低端,氣候臨界點進入激活狀態;若達到閾值區的高端,氣候臨界點進入全面崩潰狀態,會導致氣候系統發生巨大且通常不可逆的變化。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 ·諾德豪斯曾有個比喻:漂浮在水面上的獨木舟開始傾斜進水的時候尚能保持平衡,但當傾斜達到一定程度時,獨木舟就會傾覆——造成這個不可逆後果的傾斜角就是臨界點。
《2025年全球臨界點報告》着重分析了生態系統最可能觸發的6個氣候臨界點——
熱帶珊瑚礁退化:海水溫度升高和海洋酸化是導致珊瑚白化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西南極洲冰蓋融化:該冰蓋的融化速度正在加速,可能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海洋副極地環流對流減弱:這種對流減弱可能對海洋的全球熱量和鹽分分佈產生重大影響。
大西洋經向翻轉環流減弱:這是一個關鍵的海洋環流系統,其減弱會影響全球氣候模式,特別是歐洲和北美的氣候。
山地冰川退化:全球山地冰川的消融是全球變暖的明顯標誌之一,並威脅到依賴冰川融水作爲水源的地區。
亞馬孫雨林崩潰:持續的森林砍伐和乾旱可能導致大片森林轉化爲草原,從而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並影響區域和全球氣候。
突破臨界點將引發連鎖反應
氣候臨界點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不可逆,所帶來的變化也是永久性的。一個氣候臨界點被突破,氣候變化可能轉爲更加陡峭的非線性指數級變化。也就是說,在到達氣候臨界點之前,避免“觸發”的努力是有意義的,而一旦“觸發”,氣候系統會進入新的平衡,但不會再是原來的狀態。第二個特性是難以預測最後一根稻草失去的時機。這也是最危險的一點:儘管人們知道危險將會來臨,卻無法準確預見何時到來。當人們真正身處危險時,氣候臨界點往往已經被觸發。
最令科學家擔憂的是,一個氣候臨界點的到來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引發冰川崩塌、永久凍土融化、季風系統破壞以及熱帶雨林和珊瑚礁死亡等其他氣候臨界點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尤其是這種連鎖反應可能會危及一個至關重要的“地球空調”,即大西洋經向翻轉環流(AMOC)。AMOC是由海水溫度與鹽度差異驅動的全球性海洋環流系統,它通過北大西洋暖流將赤道熱能輸送至北大西洋高緯度地區,表層海水在向北流動過程中因蒸發作用鹽度逐漸升高,最終在格陵蘭島附近因低溫高鹽特性下沉形成深層迴流,對維持歐洲及北美東北部溫和氣候具有關鍵作用。
舉個例子,氣候臨界點到來,北極冰原和格陵蘭冰蓋融化,向北大西洋注入大量淡水,可能導致AMOC減弱。AMOC減弱會使全球熱量重新分佈,減少向北半球輸送的熱量,將更多熱量留在南半球的海洋中。而這種熱量重新分佈的改變,會進一步加速南極冰蓋的融化。
總之,各個氣候臨界點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一個氣候臨界點的突破很有可能觸發其他氣候臨界點,即一個事件觸發下一個事件,最終導致全球氣候模式發生劇烈、廣泛的變化。
“氣候臨界點”是需嚴肅對待的風險
世界氣象組織發佈的《溫室氣體公報》指出,2024年大氣中二氧化碳水平創歷史新高,達423.9ppm(百萬分比濃度),較2023年增加3.5ppm,爲1957年有現代觀測以來最大年度增幅。世界氣象組織官員表示,上一次地球出現如此高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在300萬至500萬年前,當時地球上還沒有人類。2024年全球年均甲烷濃度爲1942ppb(十億分比濃度),也創下歷史新高。二氧化碳對溫升的貢獻佔76%,甲烷氣體對溫升的貢獻佔16%。
可以預見,隨着二氧化碳水平不斷升高,陸地生態系統和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逐漸減弱,地球可能進入一個“氣候惡性循環”,進一步加速全球變暖和氣候臨界點的到來。
其實,近些年關於“全球變暖是否被誇大”“氣候臨界點是否存在”一直存在爭議。 目前,全球主流科學界基於持續的觀測和研究,對此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共識。簡單總結就是:“全球變暖誇大論”缺乏科學證據支持,“氣候臨界點”是一個基於大量研究、需要嚴肅對待的緊迫風險。
總而言之,全球變暖已成爲全球科學共識,氣候變化的影響也有充分科學數據支撐。圍繞全球變暖與氣候臨界點的爭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科學研究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氣候模型再精緻,也無法準確預測未來氣候變化的具體情況;另一方面,現代專業氣溫記錄最早只能追溯到19世紀中葉。
二是不同陣營的觀點及背後因素。支持全球變暖的陣營是主流,認爲全球變暖是工業碳排放造成的,會引發環境災難,背後不乏新能源產業的支持。反對陣營則質疑全球變暖的真實性,認爲碳排放與氣溫變化關係不大,不相信會引發環境災難,背後有傳統能源產業的支持。
積極臨界點存在巨大潛力
科學研究警告人們,生態系統正在逼近危險的氣候臨界點,然而,科學研究也展示了積極臨界點(Positive tipping points)的巨大潛力:政策、技術、金融和行爲方面的自我強化轉變,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推動變革。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願景就是,將人們對氣候臨界點的認知從恐懼轉變爲希望。
積極臨界點是與破壞性臨界點(如珊瑚礁退化、冰蓋融化)相對的概念,指通過社會、技術或政策變革引發的正向加速效應,可幫助緩解或逆轉氣候危機的臨界點。這類臨界點強調通過人類行動觸發系統性轉變,例如綠色技術的推廣和普及能形成自我強化的良性循環,降低碳排放並加速能源轉型,以應對全球變暖等挑戰。
當前,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電池儲能熱泵等綠色技術政策的普及,都是轉型發展的方向。 比如,電力和交通運輸行業正在經歷轉型,鼓勵全球範圍內太陽能光伏和風能的普及,經濟戰略和金融財政政策也在支持積極臨界點的政策,以及不同技術和市場的社會轉型。
公衆對氣候危機的關注和擔憂與日俱增,生態系統恢復、可持續消費模式的推廣等亦可觸發自然與社會系統的正向反饋循環。此次,熱帶珊瑚礁的大規模死亡是警鐘,若不立即採取果斷行動,亞馬孫雨林、冰蓋和洋流的喪失將真正給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言以蔽之,我們必須防止不可逆轉的氣候臨界點損害,同時也要觸發積極臨界點,推動社會走向低碳、韌性發展和包容性繁榮的未來。
北京日報記者 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