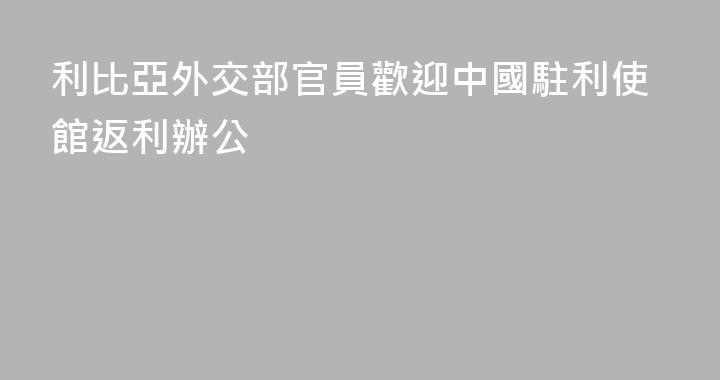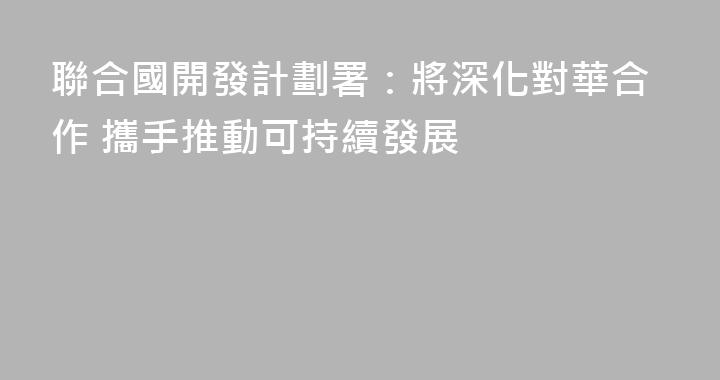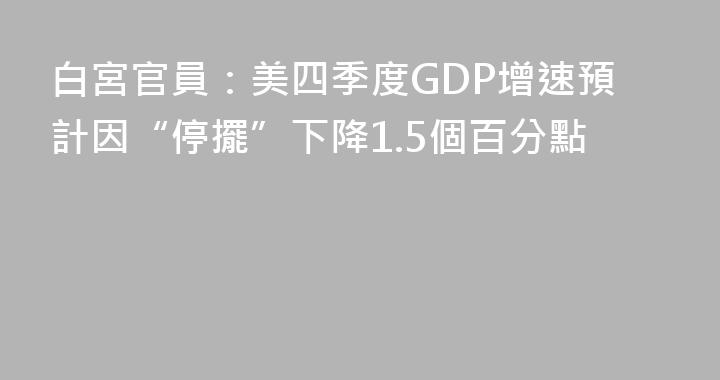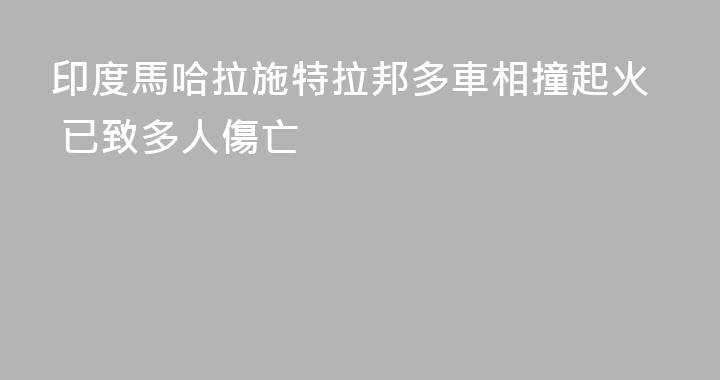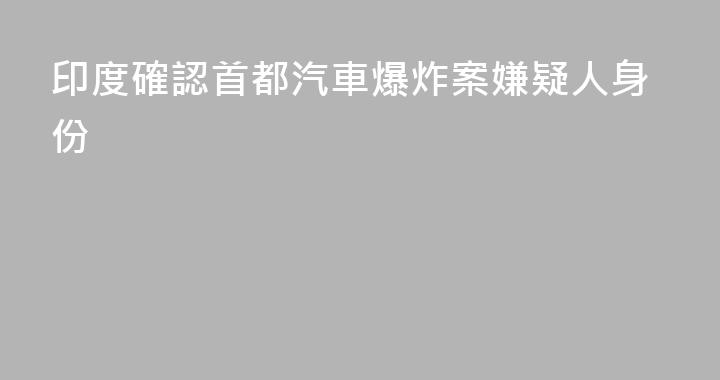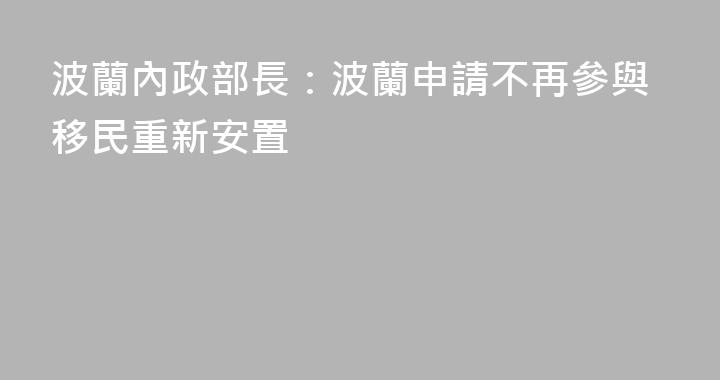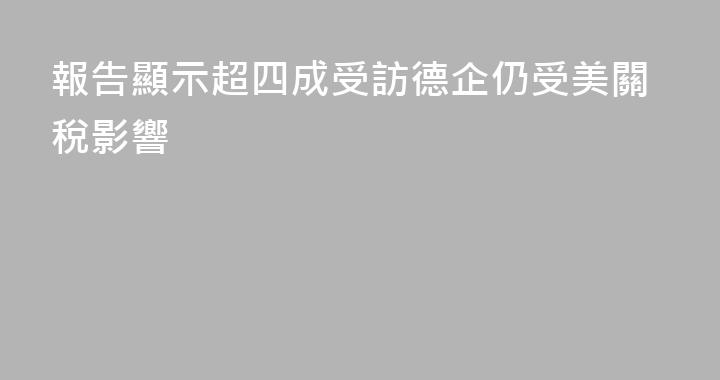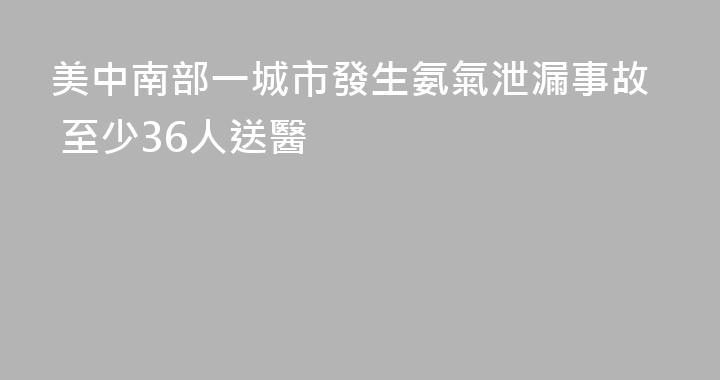【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白雲怡】雖然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達成的加沙停火第一階段協議本月10日生效,但之後雙方不斷指責對方違反協議。以方18日稱,在哈馬斯解除武裝、加沙地帶實現“非軍事化”之前,加沙戰事結束不了。輿論普遍認爲,此次停火併非衝突終點,而是各方新一輪政治、軍事與人道博弈的起點。從停火協議的執行,到後續加沙的治理與權力佈局,再到中東地區秩序面臨的變化,很多現實問題與不確定性擺在各方面前。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學者葉茲德·薩伊格此前曾作爲巴方代表參加巴以和談。《環球時報》記者日前對他進行專訪,聽他分析加沙局勢的前景。
“需要有一個具備實際治理能力的機構”
環球時報:隨着以色列與哈馬斯達成加沙停火第一階段協議,持續兩年的新一輪巴以衝突出現轉折。接下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加沙未來由誰來治理?有哈馬斯高級官員透露,該組織準備放棄在加沙地帶的治理權,這意味着什麼?您怎麼看未來加沙的治理問題?
薩伊格:加沙治理將是一個巨大挑戰。事實上,自2007年以來,治理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就不再管理加沙,它基本上失去了對加沙的治理能力並缺乏提供基本服務的經驗。在此期間,是哈馬斯在該地區建立了各類機構,負責市場監管、能源供應、市政服務、教育等各項事務,並在加沙進行了住宅和學校建設。
在這一背景下,要讓加沙的市場重新運轉起來,讓進出口恢復,就需要有一個具備實際治理能力的機構。美國的計劃是成立一個國際治理機構,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即使可以邀請外國人士組建治理委員會,具體的執行工作仍必須由當地的巴勒斯坦人承擔。然而,我們很難在當地找到擁有衛生、供水、交通、醫療、教育等領域工作經驗的普通民衆,更不要提該地區還面臨處理戰爭留下的有毒物質和未爆炸彈藥等艱鉅的工作。
要完成上述龐大的治理和行政任務,不可避免地要依賴過去18年來曾在哈馬斯及其下屬機構工作過的人員,以及有相關經驗的本地民間社會組織。因此,我認爲哈馬斯高官所說的“放棄治理權”,實際上指的是放棄一種正式的治理角色,如哈馬斯不再直接任命官員或部門負責人,但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不啓用那些曾在哈馬斯機構中工作過的人員,要在加沙重建任何形式的治理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環球時報:哈馬斯一直拒絕徹底解除武裝。您認爲這意味着什麼?對局勢有什麼影響?
薩伊格:哈馬斯一直強烈抗拒徹底解除武裝。不過,尚不清楚他們是否會接受部分解除武裝。
我認爲在這個問題上有達成某種妥協的可能性。“哈馬斯構成重大軍事威脅”的說法太誇張了。與此同時,哈馬斯顯然也不願把安全寄託在以色列軍方和政治領導層身上——後者曾多次破壞停火談判,甚至在今年3月還單方面廢除停火協議。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一年裏,以色列一直在武裝加沙當地的部落。就在上週,我還聽到一名以色列將軍在電視直播中聲稱,這些部落已經“控制了加沙80%的地區”。儘管我認爲這有誇張和宣傳的成分,但它顯示出加沙爆發內戰的風險正在上升。一旦哈馬斯完全解除武裝,可能遭到這些部落的攻擊。所以我認爲在哈馬斯解除武裝的問題上,我們需要一個更妥善的處理方法。
“有可能陷入一種新的僵局,即停火之後的後續行動難以落實”
環球時報:您認爲當前的停火協議是否能持久?加沙局勢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和風險是什麼?
薩伊格:在未來幾天、幾周,甚至是一兩個月內,維持停火應該都沒有太大問題,因爲美國正在強力干預此事,投入了大量政治資本,力圖維持停火。 不過,接下來,我們有可能陷入一種新的僵局,即停火之後的後續行動難以落實。比如接下來應該立即執行的重要環節——在加沙部署國際穩定部隊。這一步至關重要,它能爲加沙提供安全保障,防止以色列再次入侵。但截至目前,這一步還沒能做到。
在此之後,還應成立國際治理機構,負責加沙的重建和經濟復甦,並監督創建一個巴勒斯坦的治理機制。此外,還有保障加沙居民自由進出,推動經濟重建,讓加沙重新獲得資金、能源和食品供應,幫助加沙重新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這些任務對真正改變加沙局勢至關重要。然而,以色列能否接受這些,讓停火進入第二階段,對此我抱有很大疑問。
我們必須儘快推動加沙停火以後的後續行動,否則巴以停火將變成類似黎巴嫩的局面——雖然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達成了停火協議,但過去一年來,以色列仍幾乎每天都在黎巴嫩境內襲擊真主黨目標。希望加沙不要面臨同樣的命運。
“即使以色列可以對七八個國家展開軍事攻擊,但它無法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環球時報:從地區的角度來看,這次停火對中東局勢有標誌性的意義嗎?在您看來,衝突爆發兩年後,中東局勢發生了哪些重大、持久的變化?
薩伊格:過去兩年,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最顯著的變化是黎巴嫩真主黨的軍事力量被大幅削弱,以及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明顯下降。
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海灣國家作爲重要地緣政治行爲體的崛起,特別是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海灣國家雖然一向對伊朗心存疑慮,但在以色列的持續攻擊下,它們不希望戰爭蔓延到海灣地區。在今年9月以色列對卡塔爾展開直接襲擊後,海灣國家展現出了高度團結一致的態度。
同樣有意思的變化是美國處理中東問題的方式。美國與海灣國家有着廣泛的往來與商業利益,華盛頓現在也致力於加強與海灣國家的關係,特別是與沙特和卡塔爾的關係。這背後不僅涉及能源與軍售,還包括美國希望獲得的各類商業機會與合同。
縱觀過去近80年的歷史就會發現,當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以色列的行動發生衝突時,美國往往會對以色列施加壓力。例如1956年,共和黨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強烈要求以色列結束對埃及的侵略;1991年,美國也曾向以色列施壓,迫使其加入和平進程。歷史多次證明,當以色列的行爲損害美國國家利益時,華盛頓會獨立於以色列政治意願採取行動。這也意味着即使以色列可以對七八個國家展開軍事攻擊,但它無法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