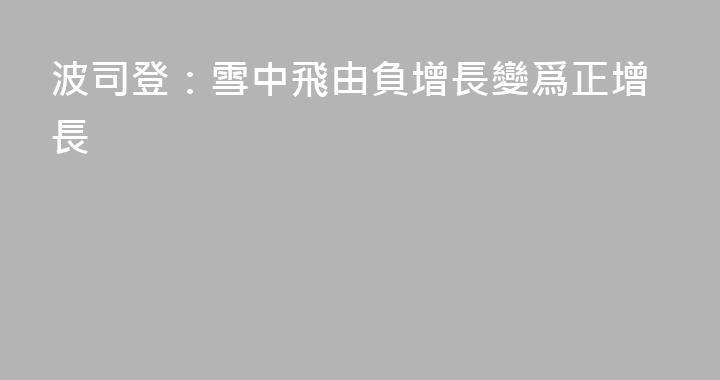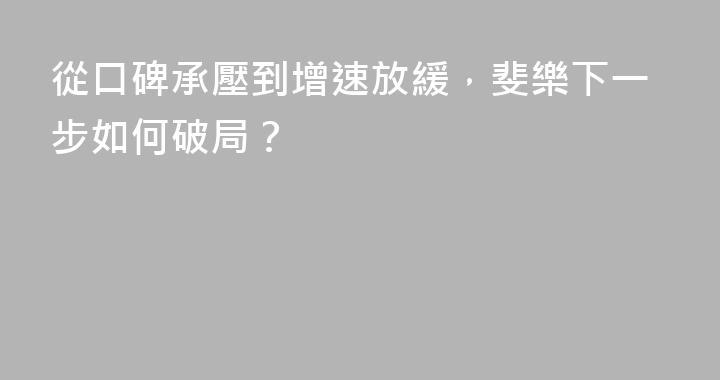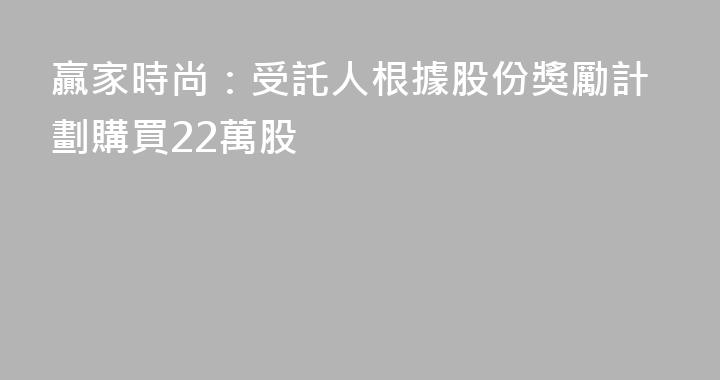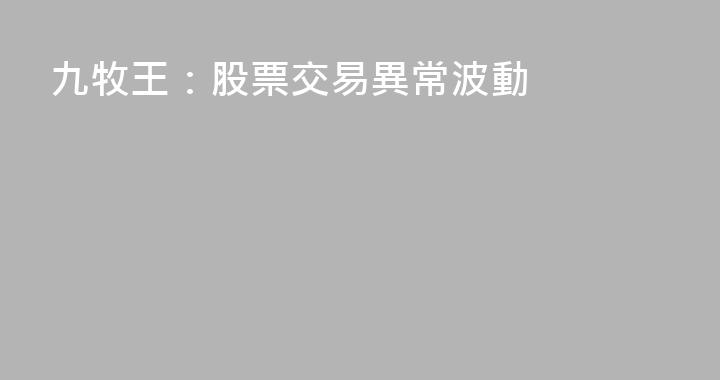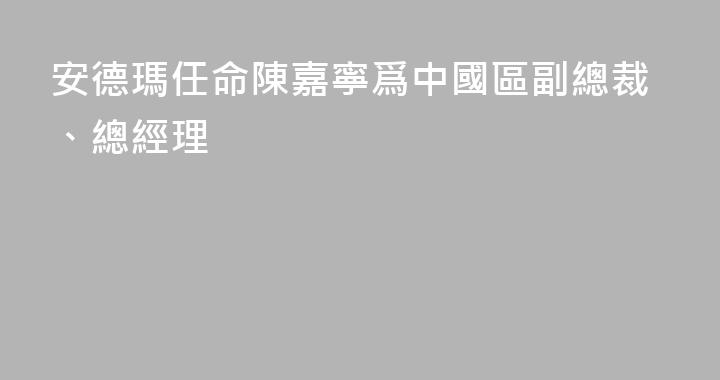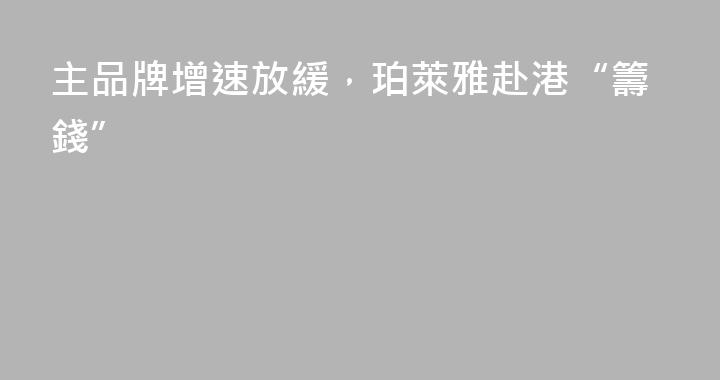本報記者 沈思怡
秋收剛過,奉賢區奉城鎮朱新村的村民發現,村裏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豐收的竟然是上海罕見的高粱,同一塊土地上,三個月前種的是藍草,六個月前是未曾見過的紅色鮮花。這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是誰種的?能派啥用場?
高粱用於發酵,藍草用於製作藍靛,而紅色的花則是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帶來中原的紅花,是古代中國製作“紅色”的重要染料。把紅花帶到村裏的“異鄉人”是邵旻,她是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副教授,是去年搬來朱新村的“村民”,也是古法植染的研究者。12月,採摘下的紅花經發酵、酸鹼法制餅後成爲染料,邵旻的小院裏,晾曬出各種紅色絲綢。至此,明代古籍《天工開物》中記載的“真紅”,在現代有了具象化的呈現。

邵旻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傳統服飾色彩、紋樣、形制。文獻古籍裏,中國傳統色彩常有詩意的表述:天水碧、海天霞、梅染、落慄,與之對應的是黃袍、紅袖、烏紗、青衫……它們描繪着古人豐富多彩的服飾世界,印證了中國古代發達的植物染色技術。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這些曾鮮豔的中國色隨着手藝失傳及工業化而逐漸黯淡,化作古書上的白紙黑字。邵旻想找回中國色彩的DNA。在村裏,她回到生產方式的源頭,從栽種草本植物到復刻植染工藝,古籍中的色彩在她的染缸裏不斷呈現,還原出灰暗文物背後更龐大的、流光溢彩的中國通史。
中草藥裏的色彩基因
邵旻租住的小院跟普通農民房並無不同,但庭院裏有染缸,竹竿上晾曬着青黃漸變的真絲布料,房屋後4畝田地裏種的是紅花、蓼藍、板藍、藎草、茜草、高粱等草本植物。它們是中草藥,也是植物染料。
植物染又稱草木染,主要利用植物所含的天然色素製成染液,是中國傳統的織物染色方式。植染在周朝時便有歷史記載,後隨歷代工藝不斷成熟,中國色更爲豐富。清代的《雪宧繡譜》已出現各類色彩名稱共計704種。
170多年前,工業革命帶來化學染劑,在絕對高效高產的衝擊下,淪爲落後生產方式的植物染逐漸被淘汰。“傳統技藝的失傳非常可惜,現代人無法親眼看見傳統中國色的真容,也是歷史研究的缺憾。”邵旻說。於是,從2011年起,她就下定決心,要“追回”這項即將逝去的技藝。重拾植物染,第一步是“植物”。邵旻說,近些年,全世界植染工藝都面臨凋敝消亡的危機,同步消亡的還有曾用於染色的植物。
“藥染同源,《本草綱目》記載,很多古代染劑植物都同時是中藥材,隨之延續至今。”邵旻坦言,探索植染的第一步,就始於中藥店,“紅花、黃櫨、鬱金等很多重要的植物染材都能買到”。但這也有侷限,如中藥店只能買到熟地黃、乾紅花,而據《齊民要術》記載,染出御黃(古代皇帝龍袍專用的黃色),需用生地黃;而染出深色的玫紅,則需將新鮮紅花製成花餅,進而發酵。2022年,邵旻從靜安區的老弄堂搬到奉城鎮朱新村,租下農家小院和4畝地,從種植草本開始,將研究推得更深一步。
與歷史古籍不斷逼近
在中國傳統植染體系中,青、黃、赤、白、黑稱爲五色,通過五色混合,再攫取其他顏色。邵旻說,同種色系背後還有多種植物,如黑色系染劑有胡桃、橡木、鼠尾草等。處理不同染材的工藝也各有千秋。邵旻舉例,有相對容易的,如搗碎新鮮絲瓜枝葉擠汁,可染出淡綠色;用黃櫨薄染時,可獲象牙色,若將黃櫨染後過鹼水,可染出金黃色。也有複雜的。如處理新鮮紅花,要先淘洗濾幹,除去不溶於水的黃色素,再加入鹼水分離出紅色素,最後加酸中和,方能染紅。
當然,古籍不會記載酸鹼溶液的具體用量,植染者只能在不斷試錯中琢磨。邵旻坦言,染出穩定的顏色常需要四到五年。
顏色背後的文化通史
邵旻的工作臺上陳列一排飽和度、色相不一的紅色染物,來訪者好奇翻看時,她會詳細地介紹哪些是漢代的紅,哪些又是唐代、明代的紅。
既已無證可考,植染者又何以確定染出的顏色,就是古書所記載的那抹色彩?“的確,我永遠也沒法知道。”歷史長河就像是一口井,植染者對着井喊,沒有回答,卻有回聲——邵旻相信歷史是能互相佐證的。她告訴記者,以紅色爲例,漢代之前,中國染紅用茜草;陸上絲綢之路讓紅花成爲漢代主流紅色染劑;到了唐代,原產自東印度與馬來半島的蘇木隨着海上絲綢之路大量輸入中原,成爲重要染料。不同染材決定了顏色的基礎。
文化背景也值得參考。如在唐代及明代的醫學文獻中,均記載了用蘇木治療血暈的驗方,除蘇木本身入藥,情況危急時還可取緋衣煮汁服用。這也能佐證,最晚自唐代起,蘇木已是兼顧染材和藥材的重要本草植物。在色相及飽和度等細節上,唐朝服飾風格崇尚華貴,色彩明快鮮豔,染出來的紅也應是越鮮亮越貼近當時包容開放的時代特徵。“顏色的成型和文化、貿易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歷史環環相扣,總能找到對的方向。”
當植染者不再固執糾結於色彩還原度本身,往往能走得更深,發現植物、色彩背後那套更爲龐大的中國古代歷朝社會政治經濟與禮制體系。比如,爲何稱天玄而地黃;又如,“古人庶人服黃,至唐時,惟人主黃袍”,最易獲得染料的黃色,是如何在禮制上實現了庶人到皇家壟斷的跨越。邵旻意識到,當她對顏色背後的故事提出追問時,收穫的回答是一部浩瀚的中國文化通史。這也成了邵旻深耕植染的新方向。
希望研究能實現閉環
朱新村很多村民,都認識她。有村民曾被邵旻僱來幫忙採集紅花;也有村民給邵旻帶去椑柿、絲瓜、蓮藕等,既補充她的染料庫,自己也多份收益;還有村民種上了邵旻給的草本植物種子,田地裏長出不少稀奇玩意。邵旻還在村裏帶動了一場“文藝復興”。不久前,她買了一百斤棉花,從村裏收了兩輛保存完好的紡車,請一羣會用紡車的村民演示用法,老太太們得以展露深藏已久的老手藝。“我想帶着她們一起紡布染紗,讓織布這項傳統技能也能傳承下去。”
她的植染工作室也已成爲朱新村的特色IP,讓植染這項絕學吸引更多人來到鄉村,這不僅能爲村裏有幾處即將開放的民宿引流,也讓這項中國傳統技藝走進更多現代人的生活,得以延續流傳。
邵旻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實現閉環。她想將植染出的顏色數字化,讓中國傳統色隨着更多美學設計及應用,被全世界欣賞熟知。她還想做自己的纖維藝術作品展和文創品牌,讓物質載體賦予色彩具象化表達。“比起單純商業化,我更希望這些作品能展陳在美術館或博物館中,帶觀衆窺見色彩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