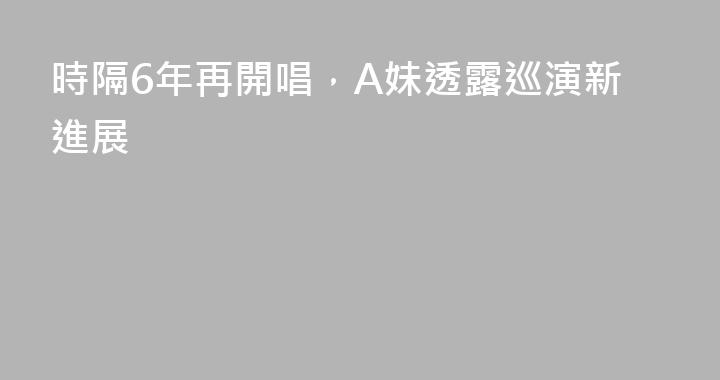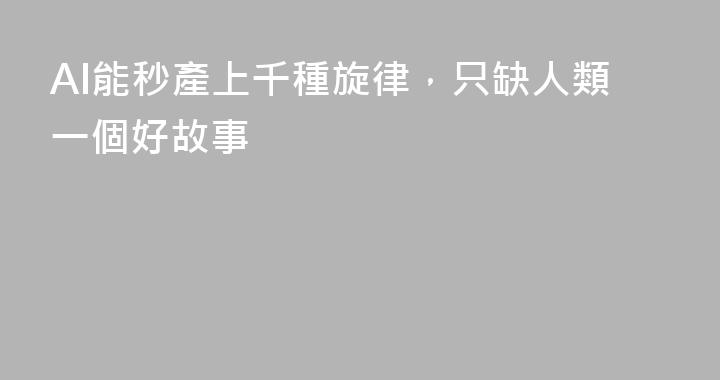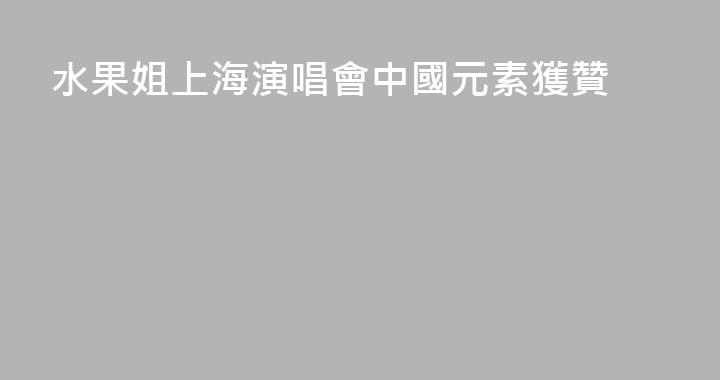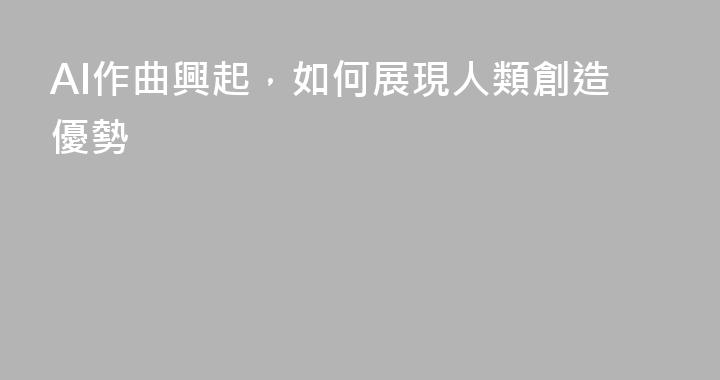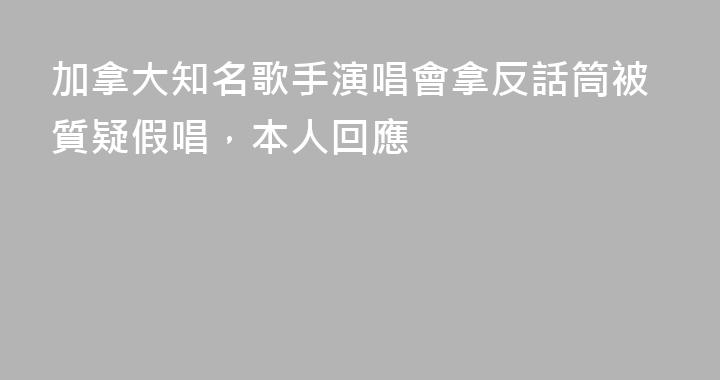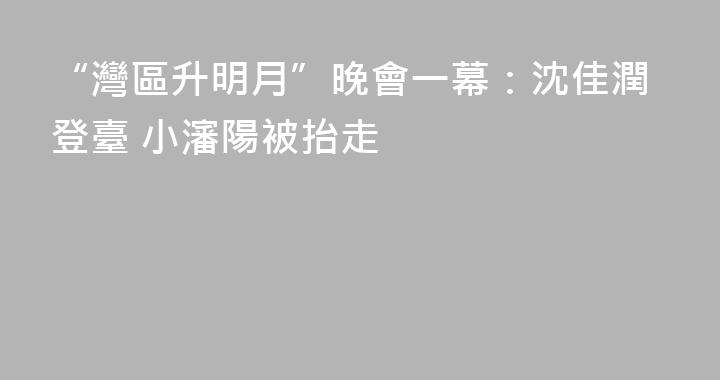“趙麗穎不再是過去的趙麗穎了。”

張藝謀的這句評價,馮小剛也意識到了。
19年前,她剛好19歲,是素人,參加選秀,成爲馮小剛組冠軍,方纔出道;如今,這位青澀的河北姑娘,已成爲手握飛天獎、金鷹獎、百花獎等衆多獎項的萬衆矚目的女演員。
兜兜轉轉多年,一個大明星,一個大導演,緣分甚深的兩人,合作也算水到渠成。《向陽·花》去年拍攝,今年清明檔上映,併成爲該檔期國產新片冠軍,更是達成春節檔後首部破億元國產電影的成就。
但1.12億元票房及豆瓣6.6分的評價,也實在談不上理想。對演員而言,《向陽·花》中的母親“高月香”一角,更像是趙麗穎過往銀幕形象的重複,而非突破。
她是被困住了嗎?
壹
“向陽花”是女子監獄文藝表演隊的名稱,是刑滿釋放人員的微信羣名,是她們重獲新生之後的生計所在——向陽花洗車行,更是趙麗穎飾演的高月香和蘭西雅飾演的黑妹的人生之象徵。
她們根在泥地,風雨摧殘而不倒,寒霜威壓而不折,用血淚澆灌根部泥土,逐節生長,終於迎來自己的秋日,無畏又燦然地怒放。
整部影片就是講生在“泥地”的她們,如何實現生命的“怒放”。
泥地,即監獄和她們的來時路。
馮小剛手法老辣,僅十分鐘便交待清楚了各自的“罪”。
高月香因傳播淫穢色情罪被判刑,黑妹因盜竊罪入獄,同室牢友有沾毒的,有拐賣兒童的,不一而足。
但主角的“罪”與其他人不同,她們在道德上是“情有可原”的:
高月香被當做“彩禮”送給了瘸腿丈夫。婚後,丈夫不工作,還家暴;女兒因腦膜炎聾了。她想籌錢給女兒買一副20萬的人工耳蝸。打工時,結識了叵測之人,引入裸聊一行,雖賺的虧心錢,但爲了孩子,哪怕火坑,她亦不旋踵。
被抓,不冤枉,但可憐。
黑妹與之類似,從小被家法森嚴的犯罪團伙養大,看似是“家人”,實則是奴隸,看似是聾啞人,實則是爲了犯罪和應對警察裝的,結識了懂手語的高月香後,兩人互幫互助,結爲一體。
她們本是至善之人,奈何生不逢時,被命運糟踐,遂有牢獄之災。但囹圄沒有困住她們,反倒清洗和抵償了先前的“罪”,當監獄大門敞開,陽光普照,她們迎來了新生——
是新生,更是血淚,故事來到第二幕。
丈夫遺棄的孩子,被福利院收養。高月香想去看望孩子,卻被園長告知,你沒錢沒房,不如不打擾。
想要獲得“打擾”的權利,就得賺錢,謀生,立足,成個人樣。可犯罪前科,成了她不得不揹負的隱形監獄:
在酒店做保潔,被污衊偷竊手錶,要求脫衣自證清白,哪怕誤會澄清,經理還是將她掃地出門。
在街邊賣藥酒,車廂裏跳豔舞,卻遭遇噁心老闆,剋扣工錢不說,甚至還想姦污她,暴打她。
與黑妹相依爲命,住八百一月的漏雨危樓,扛垃圾袋,踩縫紉機,推銷防盜鎖,好不容易有了起色,黑妹的盜賊“老爹”找到她,軟禁她,救不出,逃不掉,“老爹”甚至還要扣押她們,讓兩人代孕產子,以此贖身。
終於,高月香忍無可忍,抄起“老爹”供奉的大元寶,砸向了那張不肯放過她們、不肯給條活路的象徵罪惡的臉。
她二次入獄。
高月香以破釜沉舟的勇氣與狠辣,贖回了黑妹的人生,洗清了周遭的淤泥,六年後出獄,她終於迎來了真正的、沒有負擔的新生。
而先前的血淚,早已澆灌出一個屬於她們的未來——向陽花洗車行,女兒的人工耳蝸及關羽神像前的大結義與大團圓。
女性羣像,女性敘事,女性向陽,也是向死而生,馮小剛的新片不同以往,陌生得像是平行時空的馮小剛拍的。而這些女演員,其表演可圈可點,尤以趙麗穎和蘭西雅突出。
蘭西雅有一股不被馴服的野性,趙麗穎亦復如是,但更爲內斂,因爲她必須兼顧母性的柔光,這對演員來說,要求更高,標準更高。顯然,趙麗穎扛住了大銀幕的凝視:
行路時,感覺她隨時會被大風颳倒;
拉貨時,又像個會被麻袋掩埋的民工;
商場推銷時,標準得有點僵硬的微笑,儼然被生活操練許久;
絕望之時,那種恨意滔滔的眼神和報復,像死寂的火山突然噴發;
最令人觸動的是一個背影,監獄表演前一刻,聽見孩子的哭聲,她情難自抑地躲到衛生間,以頭撞牆,哽咽抽搐,全程看不到臉,卻讓你分明感覺到,那個羸弱的背影在顫抖。
貳
從2024年春節檔的《第二十條》開始,這一年多時間裏,我們似乎一直在銀幕上看着這樣的一個趙麗穎,掙扎、絕望、憤怒。
縱觀趙麗穎銀幕形象,早期的電影作品,諸如《女漢子真愛公式》《乘風破浪》《西遊記女兒國》等,皆是其電視形象:青春女性、國民初戀、鄰家女孩、職場新人的延續和變體。
直至2021年離婚後,她有意識地刺入現實,試圖通過更多元化的、更貼近當下時代的影視作品,剝蝕自己身上的“青春”光環。於是,其電視形象蛻變爲新時代鄉村女性、改革浪潮中的女企業家等。而這也爲她鋪平了一條可以平滑過渡到電影的道路——既證明了演員的可塑性,還保留了“偶像”的光環。
而後,張藝謀才重新“發明”了一個“趙麗穎”,屬於大銀幕的趙麗穎。
在《第二十條》中,她飾演的郝秀萍,不會說話,素顏打扮,皮膚黢黑,瘦到脫相,隨時在承受暴力和壓抑帶來的痛苦折磨。爲了給孩子籌手術費,她成了卑微的犧牲品,只能逃跑,躲藏,像一隻被標記的羊。
逼到最後,退無可退,天台上她以手語傾訴絕望,深知自己唯一可以信賴的武器,就是這條“賤命”。於是她縱身一躍,那一刻,羊成了狼。即使反撲的代價是生命,但爲了孩子和家人,這名母親,義無反顧。
郝秀萍使趙麗穎完成了突變:褪去青春的外衫,步入母性的力場。
緊隨其後的電影《浴火之路》,她又飾演了一位絕望的母親,孩子丟了,她四處追尋,和其他尋子者結成曖昧又陰暗的同盟,在灰色地帶搞錢,抑制愛的需求,爲了孩子,以身犯險,爲了孩子,持刀闖入賊窩,與罪犯纏鬥。
再到《喬妍的心事》,這部電影的題材,迥異於前兩部的現實質感,講述了一個女明星想要遮蔽、爲之糾結、不得自由的現狀與往事。演一個心不在焉又不得解脫的女明星,對趙麗穎來說,沒什麼難度。
片中,她未婚,無子,卻依然是某種母性形象的象徵。在高潮段落,她以姨母的身份,闖入狼穴,與邪惡的經紀公司老闆對峙,險被強姦,慘遭暴打,但她仍能沉着自救,隨手抄起手邊物件,砸向那個噁心的人。
臉上濺着罪人的血,懷裏抱着拼命守護的孩子,這一幕幾可成爲近兩年趙麗穎銀幕形象的強烈符號:
圓臉,白皙,瘦弱,身軀似羊,卻有逆鱗——孩子,“人有嬰(通“攖”)之,則必殺人”,因而護崽的羊,隨時可化身爲狼,奮不顧身地去廝殺。
馮小剛對趙麗穎的要求,並沒有脫離這一符號,甚至可以說,高月香是郝秀萍的延伸:兩個角色都深愛孩子,都是爲了孩子籌錢走到犯罪邊緣,都與犯罪團伙和善良的公檢法人員糾纏甚深,都在絕望的一刻,以自戕爲代價,拚命反抗不公與罪惡。
自從張藝謀發掘出趙麗穎身上獨特的母性力量,後續導演們便延續並鞏固了這一天才般的洞見,不同的僅僅是戲份長短、故事題材,當然對趙麗穎而言,最大的不同是,她從大導演的配角,成功地躋身至第一主角。
叄
被困在母親形象裏的趙麗穎,是否會厭倦這種重複?
我們不得而知。
但角色重複,就一定是壞事嗎?
也不一定。
吳京多數作品,都是以一挑十的硬漢;段奕宏、張譯多數作品,非軍即警;王寶強是鄉土喜劇,徐崢是城市喜劇,黃渤是城鄉結合部喜劇,沈騰是小城喜劇;雷佳音多是正直卻帶着一絲刁滑的小人物,肖央乾脆是苦情爸爸專業戶。
活躍在當今影壇的諸位演員,皆不得不進入角色重複的循環。可見,重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會機械重複,而毫無變化,甚至電影非但不能給角色創造表演空間,反而會因劇本、製作、導演等主創才能的缺陷,拖了演員的後腿。
高月香,就是一個被拖累的角色。
這個角色,從賣身式嫁人開始,先後遭遇女兒大病,於犯罪邊緣賺錢,不幸入獄,出獄後又被歧視、毆打、侮辱,乃至奮力一擊,二次入獄,最終才迎來曙光。論其角色弧光,其飽滿豐富、生死頓挫,遠勝趙麗穎以前的任一角色,幾乎可以稱之爲電影領域的盛明蘭和許半夏。
從左至右:高月香,盛明蘭,許半夏
可惜,棋差一着。
罪不在演員,而是劇作本身,抑或馮小剛能力欠奉。
比如角色設定上,高月香是至善之人,犯罪純屬形勢所迫,這裏不存在任何道德和人性的討論空間。
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蓮,乾淨是乾淨了,但力道明顯不足。倘若她在裸聊時,發現對方是學生——又一個孩子,良心和母愛的二難抉擇下,高月香該當如何?
類似這樣的糾結與掙扎,根本沒有。只能塑造一個道德聖潔的無辜罪人,這是馮小剛狡黠又軟弱的地方。
再者,人物關係上有一個致命缺陷,在100多分鐘的劇情裏,高月香母女從未同框,只在大結局團圓部分,母女才合體出現。也許導演有其考量,但對演員來說,無疑被剝奪了一個重要的表演機會:
愛女心切的她,從前到後只能空相思,而無對手戲。
此外,故事情節還有很多不合邏輯之處,比如一場重頭戲,高月香想與黑妹一起,拍推銷防盜鎖的視頻,以便更快地賺錢。黑妹拒絕。她堅持要拍,她堅持不拍,於是兩人鬧掰,踢板凳,掀桌子,互罵對方婊子、盜賊,以致於兩人決裂。
“決裂”是標準的電影敘事——主角組建團隊,遭遇困難,聯手抗敵,決戰前夜突然決裂,主角反省,而後召回隊友,並在最終決戰大獲全勝。所以馮小剛寫決裂戲,沒問題,有問題的是編劇技巧,過於拙劣,寧可讓主角降智和喪失同理心,都不問一句爲什麼不願意拍視頻,乾脆就吵,就暴怒,就來一場強行的“決裂”。
一個降智和沒有同理心的主角,只會讓觀衆厭惡,覺得她“有病”,又談何角色的魅力和表演的發揮?
更可嘆的是,《向陽·花》已經是趙麗穎參演的四部電影中,品質最佳、戲份最多以及表演空間最大的一部了。故而與其說是趙麗穎被困在“爲母則剛”的形象裏,不如說,那些給趙麗穎遞本子的導演編劇們,麻煩再用點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