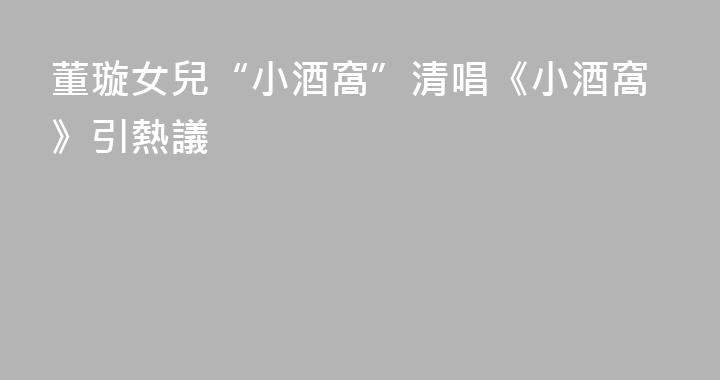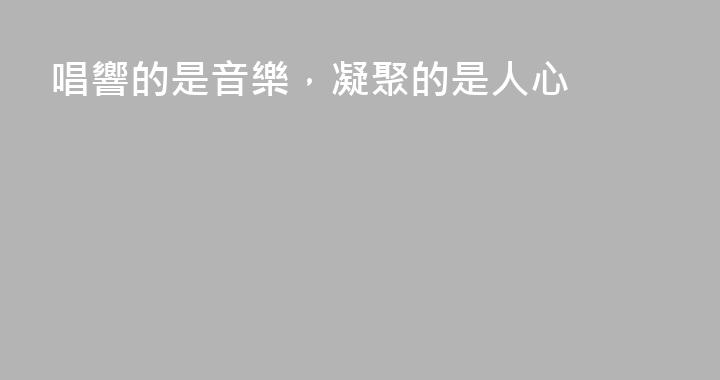黃昱寧
《我是刑警》以38集的體量,勾勒中國刑偵司法進化史,包括技術和體制,以及圍繞這兩者伸展出的世態與人心。劇中刻畫了老中青三代一線刑警們對於刑偵事業的投入與執着,警魂薪火相傳。
我不是超人
從第一集開始,《我是刑警》就跟懸疑推理類型劇劃清了界線。
1995年春節礦場的一場未遂搶劫工資款大案,搭上十幾條人命,現場慘絕人寰。刑警秦川和葉茂生是通過尋呼機回電才知道這個消息的。接下來的幾場戲奠定了全劇的現實主義基調:逼真的條件反射——“死人了嗎?死了幾個”;逼真的捉襟見肘——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通知警隊更多人,秦川吼一嗓子“去現場,去現場”就直奔危險而慘烈的現場;逼真的震驚與噁心——兩個刑警離開現場一出門就此起彼伏地吐了一地;以及,逼真的猶疑與顧忌——滿滿一屋子公安幹警開會,秦川在斟酌“要不要說”和“怎麼說”上花的心思,一點兒都不比研究案情更少。當他好不容易結結巴巴說出自己的看法之後,順嘴提了一句“我讀大學的時候——”,這一丁點兒“顯擺學歷”的嫌疑立馬被旁邊的葉茂生給截斷。他知道,沒有什麼職業能豁免人情世故,警察當然也一樣。
“警察也一樣”的觀感,此後常常在各種細節中浮現。
對秦川一生影響深遠的兩次戰友的犧牲——高所長和葉茂生——都是那麼猝不及防,那樣了無痕跡地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案情並不重大,意外令人扼腕,警察作爲肉身凡胎、與普通人同樣脆弱的那一面,被饒有意味地擺在了醒目的位置。
同樣地,與秦川素有嫌隙甚至一度鬧到水火不容的隊長鬍兵,在臨近退休進入交管系統時出了事故——事故的原因是路遇逃犯,胡兵在刑警“本能”的驅使下追上去,繼而在車禍中落下終身殘疾。讓秦川,也讓觀衆受到震撼的,正是這種在既往作品中並不典型的“英雄主義”。
英雄絕非天上掉下來的超人,而是長期習慣、素養和信念的積累漸漸滲入了“本能”的產物——這是《我是刑警》塑造人物的邏輯前提。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本劇營造的“罪犯世界”,同樣是緊貼現實、具體而微的。
對礦場搶劫案的主犯宋小軍和他老婆白玲的審訊先後進行,“錢哪有夠的時候”和“日子本來可以過得挺好的”這兩種價值觀通過瑣碎而充滿煙火氣的臺詞激烈碰撞;在偷運黃豆案中,無論是地道的形狀和成因,還是盜竊團伙混合了《地道戰》《水滸傳》、磁力發生器和迷信拜神的“管理”理念,都不是一般懸疑劇會關注的點;在本劇最喫重的連環槍擊搶劫案中,殺手張克寒在神出鬼沒地犯下一連串駭人聽聞的大案之餘,居然也會爲了跟老婆的關係而煩惱,甚至抽空冒險去辦了離婚手續。
這一切都在提示我們,這部電視劇裏的環境沒有“真空”的成分——在《我是刑警》中,英雄不是超人,罪犯當然也不是魔鬼。
我不是神探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決定。作爲類型文學/戲劇的重要分支,懸疑類作品的讀者/觀衆早已形成某些思維定式。一旦編導演把筆墨放在這些有可能放慢速度、降低懸念的細節上時,就必然會對收視羣體的期待構成挑戰。
在《我是刑警》中,警方和嫌犯的視角常常同時展開,尤其是劇中的幾個大案。在這樣的平行剪接之下,沒有什麼祕密是藏得住的——也無須掩藏。編導想得很清楚,堅決摒棄用“負信息差”來製造懸念(用“錯誤”或者無用的信息干擾觀衆發現真相,類似於障眼法)的經典套路。老實說,即便在很多所謂“社會派”(相對於“本格派”)的懸疑作品中,敢於將懸念機制拋棄得如此徹底,也是很少見的。
在《我是刑警》中,我們聽到最多的字眼是“摸排”,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大海撈針”。
有監控之前,警察挨家挨戶查人口,做筆錄;有監控之後,體育館裏坐滿了四千個通宵達旦看視頻的人;DNA技術剛剛興起,警方得爲了昂貴的檢驗成本去籌措經費、央求人力;哪怕到了現在,生物技術和大數據技術日漸成熟,依然會冒出清江爆炸案這樣用新技術難以完全覆蓋的問題,還是需要刑警們老老實實地打格子、擴範圍,直到否定完所有能否定的東西,才能剩下唯一的“肯定”。
秦川用他滿臉的疲憊和直不起來的腰告訴我們:福爾摩斯一眼便能鎖定嫌犯身份,波洛優雅地聊上幾場天便能逼兇手露出馬腳,以及馬洛在城市邊緣一杯接一杯灌下的烈酒——凡此種種,在真實的現代刑偵環境中,恐怕只能發揮其審美價值。
第15集,秦川在排查過程中試圖“還原”嫌犯的路線,屏幕上展現了一組嫺熟流暢的快切鏡頭,用特效“凝固”秦川周遭的人和物,只有秦川跟着“兇手”在其中穿梭——這是現代“神探”劇經常使用的超現實手法,在《福爾摩斯》或者《唐探》系列裏俯拾皆是。整個畫面看起來就好像摘蟠桃的仙女被定身法困在原地,任憑孫悟空在其中恣意行走。與全劇樸實的、近乎紀錄片的基調相比,這一組鏡頭顯得頗爲異類。
好在《我是刑警》對這類手法使用得很少也很剋制。在那幾十秒裏,被“定身法”包圍的秦川並不像齊天大聖那麼威風,反而顯得惶惑無助,很快就在半路上跟丟了前方的目標——“神探”迅速變回凡人。秦川或許獲得了一點靈感,但離水落石出還相當遙遠。
這一組鏡頭的新穎之處在於——它並沒有出現在撥雲見日的那一刻,而是從此開啓了長達八年的艱苦摸排和無悔追蹤。在這部劇裏,沒有一個警察頭上頂着神探的光環,也沒有一朵雲,是依靠突然發亮的金手指來撥開的。
我不只是個體
第14集的敘事節奏同樣耐人尋味。秦川在接下張克寒大案之前,居然用了整整一集,才下定決心——這樣寫會不會拖慢節奏?敘事的必要性在哪裏?
耐心看下去,我們會發現,讓秦川糾結也讓武英德老師過意不去的原因有兩點:其一,接了這個案子,秦川個人的成長可能會轉向,中斷原來從地方到省部的垂直升遷路徑,轉而到不同的地方督辦大案要案,面對各種陌生的環境。其二,這陌生的環境意味着長期形成的條塊分割,意味着在尚不完善的機制中四處碰壁。在劇中,刑偵專家已經在技術上認定應該儘快併案協查,卻遲遲得不到地方的配合。
一邊是具有很強反偵察能力的案犯看準了條塊分割、各自爲政的漏洞,四處流竄犯案;另一邊則是幹警在無效的推諉中互相消耗。所以病牀上的武老師緊緊拉住秦川的手——他要交出去的不僅是一樁大案,更是整合資源、興利除弊的重擔。秦川也很清楚,他一旦接過這副重擔,那從此要面對的就不再只是技術、罪犯和證據鏈,而是複雜關係的艱難博弈、互相拉扯,是所謂的“工作環境”問題。
於和偉飾演的秦川,用壓抑的喉音,短促的斷句,遊移而失焦的眼神,把“工作環境”這四個字咬出了力透紙背的含義: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幹不成。我越來越知道,破案子是難,但更難的,是要有工作環境,是要能調動資源。”
武老師病了一次,又傷了一次,病牀上兩次近乎“託孤”的言行(“再不搞就真的不行了”),才最終磨成了秦川的決斷。這樣的情節看起來既不跌宕也不激烈,但潛臺詞異常豐富。人物的盤桓與糾結,前景的未知與膠着,一切盡在不言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整這一集“文戲”中,演員可以調動的手段很少,聲臺形表都給塞進燜燒鍋文火慢燉——端出來的菜色,卻得具備《紅樓夢》中所說的“宛若含着千斤重的橄欖”般的表現力。於和偉做到了。他的表演讓我相信,在個體與環境的相對論中,秦川最終找準了自己的立場:每個人都不僅僅是個體,每個人都是“工作環境”的一部分。如果沒有現成的可以“幹得成事”的環境,那就通過“幹一件事”來改變它。
我就是刑警
文本細讀就像探案,在釐清了“我不是什麼”之後,離“我是什麼”和“我想表達什麼”就不遠了。
《我是刑警》的時間跨度長達30年,空間跨度遍及天南海北(都囊括在虛擬地理概念“中昌省”中),絕大部分用實景拍攝,敘事風格乍一看頗有幾分像紀錄片——然而它不是紀錄片,更不是“僞紀錄片”。
無論是煞費苦心構建的時空圖景,還是素材遴選(不看重情節的離奇曲折,能在多大程度上折射時代變遷纔是首要標準),本身就體現了強烈的敘事野心:以38集的體量,勾勒中國刑偵司法進化史,包括技術和體制,以及圍繞這兩者伸展出的世態與人心。在這樣的主題統攝下,每一個故事都是這巨大畫幅裏的一塊拼圖——它們的意義,是在與其他拼圖的互相對照和拼接中才得以凸顯的。
如此雄心勃勃的框架會不會對敘事造成壓力?當然會。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感到密度過大,有時候又覺得信息傳遞中有冗餘成分可以精簡,有時候還會看得出轉場過渡有生硬和說教的痕跡(比如第23集中通過講課的方式提出新技術環境中還需不需要老刑偵經驗的問題)。
當然,最突出的還是那個老問題:選擇這樣介於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之間的風格,是以徹底犧牲懸疑性,大量淡化戲劇性爲代價的。那麼,《我是刑警》究竟憑藉了什麼,拉住了這麼多觀衆?
靠結實的人物。作爲在這部作品中穿針引線的人物,秦川這個人物既擔負着繁重的功能性,也必須以完整的成長弧線來維持與觀衆的情感連接。清江爆炸案時期,秦川在除夕與家人通話,頭頂上滿天星斗,腳底下黑色泥土,耳邊是電話裏傳來的煙花絢爛。那片刻的釋然,人物在半夢半醒中神遊的狀態,是足以擊穿人心的神來之筆。
靠結實的細節。審訊室裏給宋小軍端來的掛着勾芡的鍋包肉,白玲手上的凍瘡(所以她一直在狠命地搓),張克寒對着超市監控的挑釁眼神,以及他手裏拿着的“西班牙麪包”(因此,秦川在看到這段視頻時會大喊“看,西班牙麪包,我們丟不丟人”;也因此,於和偉能把那種微妙的失控感,釋放得如此真切自然)。凡此種種,都體現了劇本、場景以及服化道的一絲不苟。這些充滿逼真細節的規定情境給了演員最充分的信念感,是所有“演技”得以充分施展的前提。更何況,走進這些情境的,是像於和偉、富大龍、丁勇岱、馬蘇這樣的好演員。
想起一個細節。秦川在會上提出“給嫌疑犯畫像”的刑偵理念,如何一步一步,一筆一筆地從茫然無緒的線索中逼近“真實”的形狀,旁邊有位刑警插嘴說——“這不是編劇該乾的事兒嗎?”
“沒錯,這活兒就像編劇!”
聽到這裏,我忍不住微笑起來。這句臺詞算不算積累了幾百萬字素材的編劇偷偷給自己的一個小獎賞?我覺得算。(作者爲作家、翻譯家、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