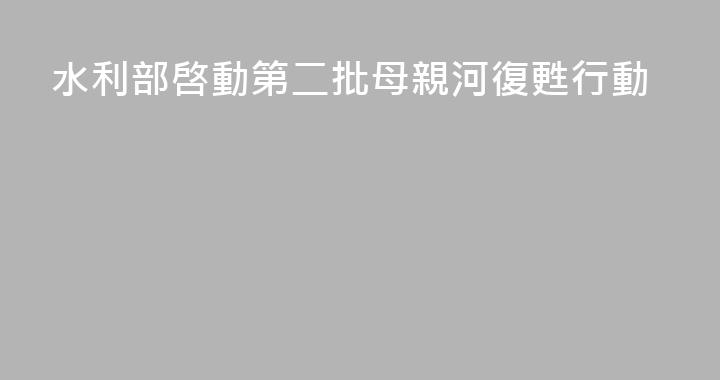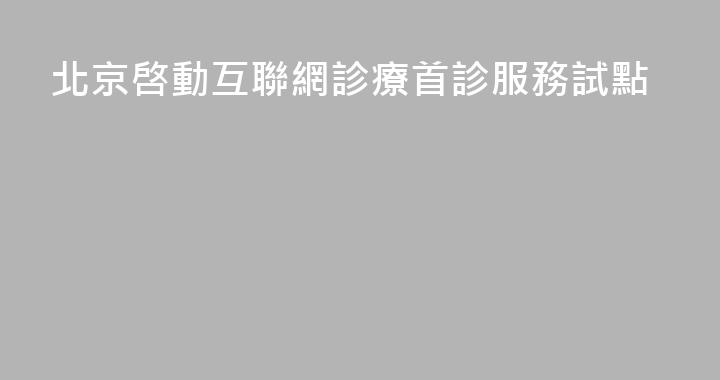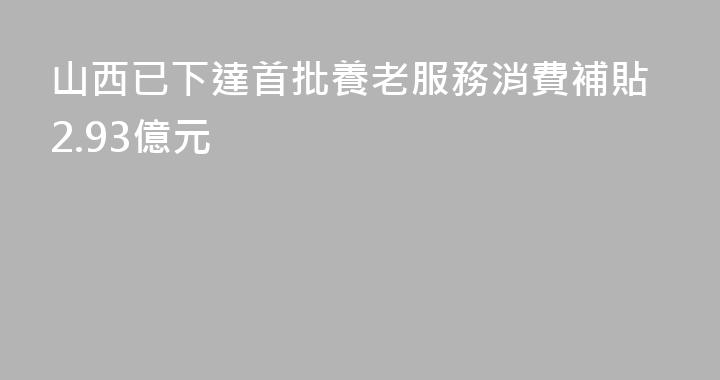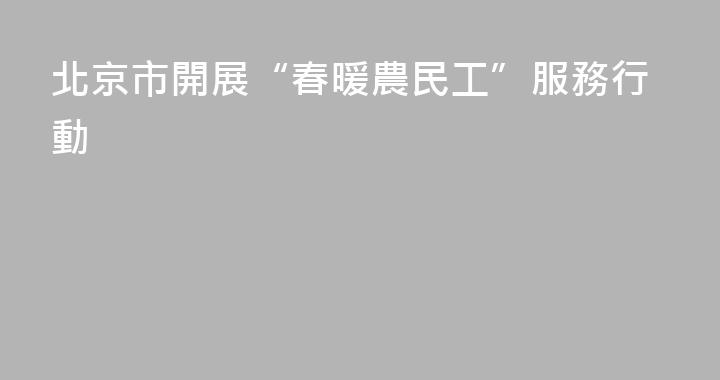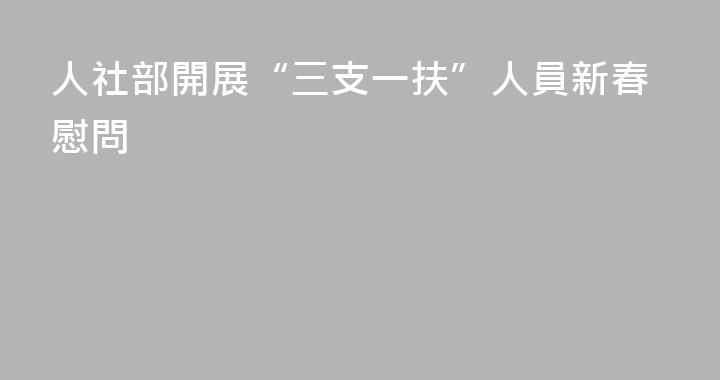【環球網報道 記者 文雯】在文學的浩瀚星空中,徐海蛟宛如一位執着的探索者,以文字爲舟,探尋歷史與童心的交匯。他的作品不僅承載着對故鄉的深情回望,更以兒童文學爲載體,傳遞着對人性、歷史與未來的深刻思考。世界讀書日即將到來之際,環球網專訪了這位多才多藝的作家,他的作品,無論是對歷史的深刻解讀,亦或是對兒童心靈的細膩描摹,都展現出他對文學的敬畏與熱愛

徐海蛟的文學之路始於小學時期的作文表揚。他回憶道:“小學時,我的作文常常在課堂上受到老師表揚,並作爲範文念出來,這種讚許給了我一個心理暗示,讓我相信自己是有寫作天分的。”到了初一,他遇到了一位文學啓蒙老師,老師的一句話深深影響了他:“我的理想是自己課堂上能夠誕生一個真正的作家。”這句話成爲他文學創作的起點。
“這種早期的鼓勵讓我相信,寫作不僅是表達自我的方式,更是一種與世界對話的途徑。”徐海蛟說道。這種信念伴隨他走過了漫長的文學之路,成爲他不斷探索和創作的動力。
徐海蛟的故鄉在他的作品中佔據了重要位置。他的《山河都記得》中,對故鄉和親人的描寫充滿了深情。他坦言:“童年和故鄉都爲寫作者提供了精神底色,儘管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早已面目全非,但它最初帶給我的影響註定是終身的。”
他進一步解釋道:“我書寫故鄉,並非爲了讚美它,而是想借助文字這條路返鄉,回到我生命的襁褓中。”通過文字,他不僅記錄了故鄉的山水與人文,更探索了自我與故鄉的深層聯繫。
徐海蛟曾獲得第四屆人民文學新人獎、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等多個重要獎項。但他對這些榮譽的看法頗爲淡然:“這些榮譽都是過去的事了,除了滿足過一段時期的虛榮,翻篇後,我覺得意義並不大。對於一個真正的寫作者來說,最大的榮譽是讀者給的,有無數真誠的讀者讀我的作品,並且在我的文字中找到慰藉與力量,這是我能想到的最令自己驕傲的事。”
他強調,讀者的認可是對他創作最大的激勵。這種對讀者的重視,使他的作品始終保持着真誠與溫暖。
徐海蛟認爲,兒童文學在文學領域中佔據着重要地位。“兒童文學首先是文學,它與所有其他的文學門類是並駕齊驅的。但由於它的受衆是天然的純真的孩童,這些讀者心智尚未經歷過生活的磨折,我們爲他們提供精神食糧時,需要考量的東西更多。”
他指出:“兒童文學比之其他的文學需要更高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需要更加出色的表達力。”在創作兒童文學時,他強調必須站在孩子的立場和視角去看待世界,喚醒自己內心的孩子,避免以俯視和傲慢的態度與孩子對話。
徐海蛟不僅是一位作家,還致力於寫作教育,形成了獨創的“基於過程的”寫作教學體系。他認爲,寫作教育對當代青少年至關重要。“我做寫作教育,是期望通過寫作這件事真正讓孩子們學會勘探自己的心靈,並且用文字這樣一種既安靜又內心化的方式與世界對話。”
他引用馬爾克斯的話:“一個會寫作的大腦和一個不會寫作的大腦是不同的。”通過寫作教育,他希望孩子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自己,表達自己,並與世界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
徐海蛟的創作理念核心在於探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人性的豐富與複雜。“我寫作的核心理念是探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探討人性的豐富與複雜,並藉助文字,與讀者一道返回人的精神原鄉。”他說道。
在不同文體之間,他找到了自己的節奏。“我目前給自己的寫作分了兩個方向,一個是歷史散文,另一個是兒童文學,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文體間如何切換呢?我的方法是按階段來,一個階段寫歷史,過一個階段,將心裏的孩子喚醒,寫兒童文學,交替進行。”
徐海蛟認爲,寫作最大的挑戰是面對無窮無盡的寂寞。“你得忍受得了這樣的寂寞,得坐得住冷板凳。它是一個人的事業,一個人走一條無盡的遠路,無休無止。”
他強調,作家在創作中的自我突破,唯一辦法是不重複。“題材、創作方式、觀念都得不重複,這樣的寫作纔有價值。”
徐海蛟的新作《1938回答2026》聚焦於歷史與當下的對話。創作靈感來自西南聯大和當下的孩子。“我們曾經有過十分出色的教育傳統,尤其是西南聯大,以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爲後來的新中國輸送了無數大師巨匠,而反觀當下,孩子們卻在學習與成長中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他希望通過這部作品,讓西南聯大的精神之光照亮這一代迷惘中的少年,讓他們重拾青春信念,並且更透徹地明白學習與人生的價值。
徐海蛟認爲,在現代社會中,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尤爲重要。他希望通過作品,讓無私無畏無往不前的抗戰精神和獨立包容的學習精神迴盪在21世紀20年代的青少年心靈中。
在談到AI的應用時,他認爲:“AI可以幫助我們在文化傳播,文化研究等諸多領域上做出貢獻,但人類作爲碳基生命的那個部分,應該被獨立出來,這也是人之所以稱爲人的原因。”
徐海蛟的創作是一場對歷史、童心與人性的深刻探索。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僅是故事的講述者,更是精神原鄉的守護者。他用文字記錄下那些值得珍藏的瞬間,爲讀者構建了一個既真實又充滿詩意的文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