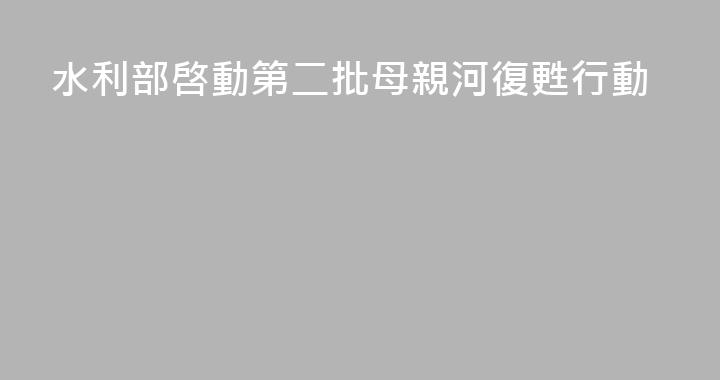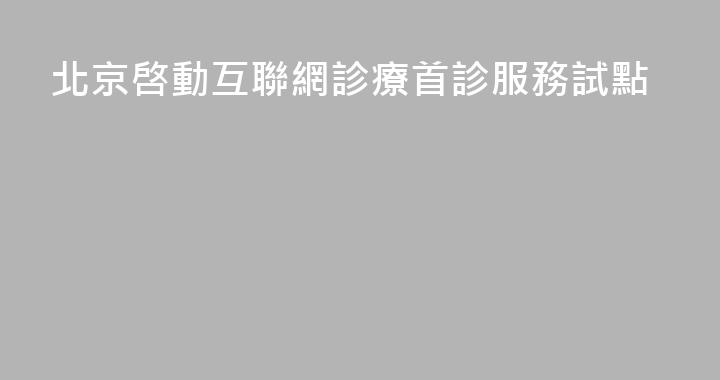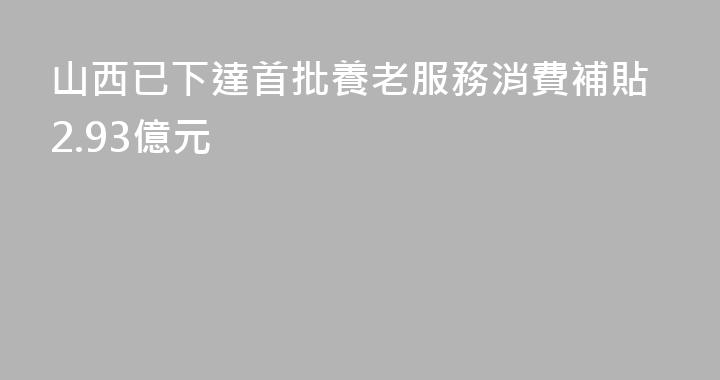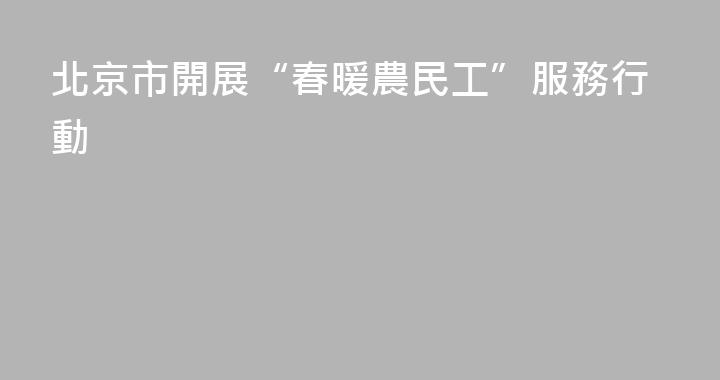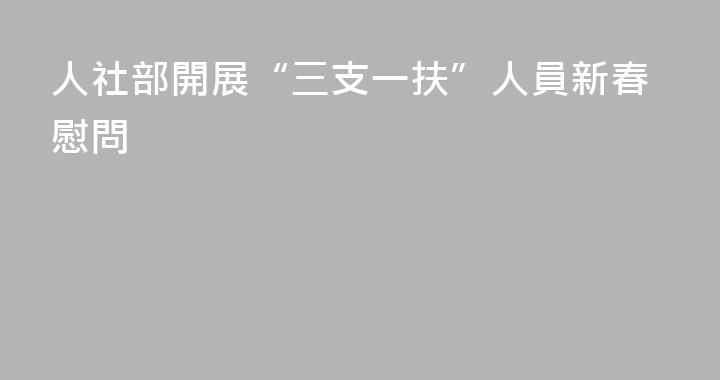【環球網報道 記者 文雯】在兒童文學的廣闊天地裏,保冬妮宛如一位執着的追夢人,用文字和畫筆爲孩子們描繪出一個個充滿詩意與遠方的世界。她的作品不僅深受國內讀者的喜愛,更走向了世界,讓全球的孩子們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世界讀書日即將到來之際,環球網專訪了這位多才多藝的作家,聽她講述創作背後的故事。

環球網:您的童年經歷對您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經歷是如何激發您走上創作之路的?
保冬妮:每一個人的童年經歷都會刻進成年以後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裏。孩子的童年無法自己選擇,但確實又影響深遠。每個孩子帶着父母和家庭教育的痕跡走向社會,成爲獨特的自己。1952年,媽媽來到《中國少年報》當記者,她也是報社最早的知心姐姐之一,那時我住在寄宿幼兒園,週六被媽媽接到東四十二條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她一邊工作,一邊從辦公室的書櫃裏拿出很多中外童書給我看。週末到家,睡覺前,媽媽有空會給我讀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普希金的詩歌。後來我上小學,媽媽買了一對大書櫃,就把她的小書架送給了我,我的書架裏慢慢積攢了很多小人書,很多小夥伴也還會來家裏看書。爸爸喜歡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他給我講孫悟空的故事,講山海經和《封神演義》《鏡花緣》,這些童年的閱讀和聆聽都帶給我對書的喜愛,整個少年時期,讀了爸爸媽媽兩個書櫃裏的絕大部分的中外名著。這些都像養料,爲日後我寫作奠定了基礎。
環球網:您不僅是一位作家,還是一位資深編審和心理諮詢師。這些職業背景如何相互融合,影響了您的創作?您認爲這些經歷爲您的寫作帶來了哪些獨特的視角?
保冬妮:我的職業生涯與雜誌和記者、編輯無法分離,那是一種積累和學習的過程。我幹過雜誌社的所有行當,從美術編輯、文字編輯、記者到編輯部主任、主編,積累了一個作品如何策劃、如何實施、如何前期採訪、後期寫作和配圖,排版、印刷、紙張和開本、銷售與活動策劃……這些每一個步驟都深刻影響了我後期的圖畫書創作。我的近20年的圖畫書創作之所以作品很豐富,具有獨特的個性特徵和審美風格,是因爲我把每一部作品的出品如像做雜誌那樣安排得前後有序,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都提前在計劃之中,我列出我最有興趣和有生活實踐基礎的主題,慢慢創作,每個作品基本都要經過兩年的創作時間,有的更長,自然題材的作品創作都在四年以上,我反覆去動物生活的地區拍攝,前期投入比較大;有幾本圖畫書創作過程也挺波折,畫家畫了六年,我們會慢慢做,慢慢等,也不着急,我們都想做出代表個性特徵的作品,不想隨意湊合。這種工作狀態是一個彼此享受創作的過程,我和畫家、圖書設計師都是好朋友,創作的過程,非常開心,從沒覺得有工作是艱難的,樂在其中是我們的常態,所以,也不用堅持,喜歡就做唄。
心理諮詢的學習早在20年前,那時是工作的需要,我帶着編輯去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學習,考心理諮詢的證書也是爲了能辦起心理諮詢的欄目。後來,我又參加了美國遊戲治療的兩年三階段的培訓,主要針對特殊兒童的治療,有了更多角度去認識兒童、瞭解兒童。這些知識都對我做0至6歲兒童的圖畫書特別有幫助,尤其針對功能性的圖畫書,可以基本做到精準到位地針對兒童關鍵期的需要和家庭教育的重點。所有的成長都有意義,因爲誰也不知道是否未來會用上這些經歷。感謝時光,送給了我很多可愛的機會。
環球網:您的“中國非遺系列”繪本獲得了廣泛的好評。您認爲這一系列成功的原因是什麼?在創作過程中,您如何確保傳統文化的精髓得以準確傳達?
保冬妮:我從來沒覺得我有成就,但有積累是真的。中國非遺圖畫書大系我做的很早,2009年大家把目光放在引進圖畫書的時候,我已經在做《小小虎頭鞋》和《虎頭帽》了。原創做的早,就可以慢慢想、慢慢做,不着急,也不用搶熱點、搶選題,因爲所有的都是冰點,這點和今天不一樣。這套書我們創作了十多年,這也是和所有涉及非遺主題的圖畫書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選取的非遺項目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孩子們玩的、用的、看得見的、摸得着的;另一個是圖畫書的延伸部分,讀完書每個孩子都可以跟家長學着玩、學着看、學着做。我認爲這樣的圖畫書纔有生命,這也是與引進圖畫書最大的區別。因爲我當時已經是《超級寶寶》圖畫書刊的主編,一門心思琢磨怎麼能找出原創圖畫書的生命所在。這套書無論是剪紙、皮影、風箏、團扇紙扇,都是孩子們認識的、玩過的、用過的;日常誰沒種過花、看過戲、遊過園林、歡度春節?想想這些我們身邊看似平常的生活,哪一個不是閃耀着非遺之光的藝術?一部戲精準傳達要找好演員,一本圖畫書的精確表達,就是要找到合適的畫家,畫家的藝術風格和個人氣質都會影像一本書的審美,所以,我會找我熟悉的朋友來參與創作,我瞭解她們的心思,熟悉她們當下的心境是不是可以接這個作品,事實證明我選的很對味,畫家們當之無愧,都恰如其分地準確到位。
環球網:您的作品不僅在國內受到歡迎,還輸出到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您如何看待中國兒童文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保冬妮:我每年都自己買機票去很多國家,我是去拍攝野生動物,但遇到書店我都會進去買書、看書。中國作品在外國的書店幾乎看不到,在外國的一些華人聚集地區的社區圖書館可以見到很少一部分;輸出並不代表在國外有非漢語的印刷量和閱讀量。我的圖畫書《咕嚕嚕涮鍋子》在德國已經有了10年的版期,德文版不斷加印,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期。中國非遺大系也輸出了韓國,期待有讀者喜歡。很多中文作家的作品在國外仍是華僑在買。普遍說來,母語非漢語的讀者對中國作家作品的認識幾乎是零,它遠沒有成爲主流文學的一部分。輸出後,當地的出版社也做不到像國內對引進版的圖書那樣大力地宣傳和推廣。隨着中國文化被更廣泛傳播和不斷被全世界人民接納,也許未來有一天,中國的兒童文學作家會被更多非漢語國家的孩子們瞭解並喜愛;我們需要視野廣闊,不斷拓展書寫的題材、探索兒童世界的深邃與廣袤,真誠地直面兒童的內心與生境,才能寫出更多好作品。
環球網:您的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外重要獎項,如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冰心文學新作獎等。這些榮譽對您的創作有哪些激勵作用?
保冬妮:我感恩大家給予我的作品的肯定和喜愛,但它們作爲一個歷史都過去了。我的創作並不來源於榮譽,而來源於不停的行走和閱讀。我覺得行走更是重要,它讓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去了解並學習我過去所陌生的領域,那纔是帶給我好奇、驚喜與心靈飛翔的地方。我的寫作也並不是爲了榮譽而寫,而是我覺得有值得與孩子們分享的生命故事,我才寫並畫下它們,做成書。我覺得見天地、見衆生、見自我的過程,纔是激勵寫作的源泉。
環球網:您的作品常常以中國傳統文化爲主題。您認爲在現代社會中,如何更好地將傳統文化融入兒童文學創作中?您希望通過作品爲孩子們傳遞怎樣的文化理念?
保冬妮:我的一部分圖畫書作品確實是以中國文化作爲外在表達形式,但即便是中國非遺圖畫書大系,其主題也有很多不同,仔細閱讀的讀者會發現其中《遊園》的主題是:兩重空間的女性再現與對比;《春扇》的主題是:扇文化與女性生活的歷史與當下的對話;《虎頭帽》的主題是:新移民在地文化與母語文化的融合;《本草》的主題是:草木之美治癒心靈……
只要是寫在地故事,無需刻意爲之,都會把中國的文化寫入作品中的,因爲我們就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每個人當下都是傳統文化不經意的攜帶者、傳承者,我們喫的飯、說的話、唱的戲、用的碗、喝的茶、過的節、穿的衣,哪一個少得了傳統文化的加持,刻意融合反而會裝模作樣顯得過分而不自然了。我覺得一切恰如其分都是剛剛好,爲孩子自然而然的寫作,別添油加醋地把味道搞的過於濃油赤醬,那樣,再好的菜,也沒有了原汁原味。
環球網:您在創作中不斷嘗試新的題材和風格。您認爲兒童文學創作者應如何在保持傳統的同時,實現創新與突破?
保冬妮:我覺得每個人都在自己熟悉的話語中講述自己得心應手的故事,創作的百花園只有百花齊放,纔是春天。創新與突破的前提是具有多元的視角和深邃的洞察力,還需要不斷在寫作形式和語言上尋找新的結構和自己的特點。
環球網:您的新作《黃河口的東方白鸛》聚焦於黃河口的生態環境和東方白鸛這一珍稀鳥類。請問您創作這部作品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保冬妮:我用油畫綜合材料創作這本圖畫書,反覆修改,用了三年時間。
以往都是我寫故事,找畫家朋友參與創作;這次,我自己動筆畫圖畫書,選擇東方白鸛,是因爲我太喜歡它們,它們太需要人類的包容和幫助了。
東方白鸛是我們國家的一級保護動物,因東方白鸛繁殖分佈區域狹窄,數量稀少,目前已處於全球瀕危狀態。每年秋冬,它往南遷徙到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但路途上經常遭到人爲的傷害,每年都有死亡的案例。黃河口溼地的所在城市東營,對東方白鸛敞開了友善而溫暖的懷抱,東方白鸛原本不會在這裏繁殖,但是生境的友好,食物的豐富,讓東方白鸛選擇了黃河口溼地成爲繁殖地,儘管這裏並沒有它們築巢的高大喬木,但是東營人把東方白鸛作爲市鳥,給與它們最大的保護和愛戴,讓出高架的電線杆搭建東方白鸛安居之所,幫助留下來繁殖的2000多隻東方白鸛,幾年累計,已經有3000幼鳥在此出生。
我是一個作家,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出一本幫助東方白鸛的書,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它們的存在,從而像黃河口溼地的人們那樣愛護鳥類、善待動物,至少不去傷害它們。這就是我做這本書的初心。
環球網:在這部作品中,您是如何將藝術創作與現實環保問題相結合的?您認爲兒童文學在環保教育中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保冬妮:藝術可以成爲探索科學實踐更深層意義的有力媒介。藝術與文學、科學的碰撞,每一次都會產生令人欣喜的思考。《黃河口的東方白鸛》直面的是現實世界裏的野保問題,我們如何瞭解這些野生鳥類的生境和習性,如何能更科學地保護生物的多樣性。這些話題在孩子年幼的時候,就和它們來討論,我在作品分享會上,所有的孩子表達的全是:我們要幫助它們,讓它們自由飛翔。兒童文學天然地與兒童的閱讀聯繫的最緊密,我們帶給兒童的閱讀不能僅僅是文學的,科學視野的廣大和深邃直至生命的本源和未來,更需要孩子們去了解、去關注、去研究。只要給孩子們這樣一個機會,孩子們都會天然地愛戴自然。
我第一次拍攝野外的東方白鸛是在天津的北大港,那是2019年3月。也是在這一年,黃河口溼地被列爲全球重要溼地之一。那次,5只東方白鸛在頭頂幾百米的上空盤旋,從相機的視窗裏可以清楚地見到它們美麗的眼睛周圍的紅色裸皮和紅色的腿。自然觀察中只要有孩子,他們一定會爲觀察的對象:鳥類和動物所驚歎,大自然對於孩子們的引領是無需語言的,一種觀察、一種親近,自然的力量就是無窮的。所以,兒童文學中需要有科學視野的環保作品、野保作品,讓沒有機會走進自然的孩子,在書中獲得閱讀的機會,去思考自然與我的關係。
環球網:在創作《黃河口的東方白鸛》的過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戰?有哪些特別的收穫?
保冬妮:創作《黃河口的東方白鸛》最大的挑戰是繪畫本身,我是一名作家,畫150x50C的大幅油畫作品是一種巨大的挑戰。但是,爲了展現黃河口溼地的廣闊,呈現遷徙路途的漫長和遙遠,這些都需要用跨頁的形式來表達視覺語言的描述。於是,一張畫的反覆覆蓋和重新繪製,是畫畫中的常態。當成書擺在我眼前的時候,我也很驚訝這是我自己畫的。我退休後學油畫,不是科班出身的我,只是從小熱愛繪畫,最大的成績就是小學獲得過我們北京海淀區的繪畫獎。但是,可以彌補專業繪畫缺陷的是,我和我丈夫、女兒都是拍攝野生鳥類和動物的愛好者,我們拍攝了大量的資料,不同的季節多次開車去東營,拍攝溼地的景觀和東方白鸛,以及書中所涉及到的那些鳥類,去觀察和寫生,這些都讓我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比我的畫家朋友們更瞭解那裏的生態。繪畫經過三年反覆的修改,一次比一次好,繪畫的水平也在不斷的提升。《黃河口的東方白鸛》裏的油畫作品,2024年、2025年兩次入選了中國油畫院雲上美術館舉辦的線下油畫展《愛繪畫·女性繪畫展》和《愛繪畫·繪畫作品展》。
我想,愛是可以改變一切的。愛自然,讓我去捕捉大自然中最靈動的一面;愛繪畫,讓我融化在色彩和線條中,去重新認識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關係,重建我的心靈世界和情感天地,也重新定義藝術、自然與女性的關係和表達。
坐在畫架前,世界是安靜的,時間是凝固的,思緒是奔湧的。雖然我沒有在藝術院校學過一天的專業美術課,但是網上油畫課的階段學習和去世界各地參拜美術館、走在荒野中的觀看,讓我有了看世界的新角度,我可以大膽地在畫布上畫下我的世界、鳥的世界,和我所熱愛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