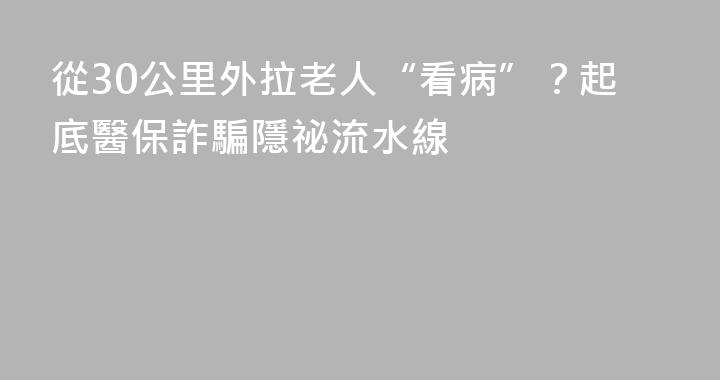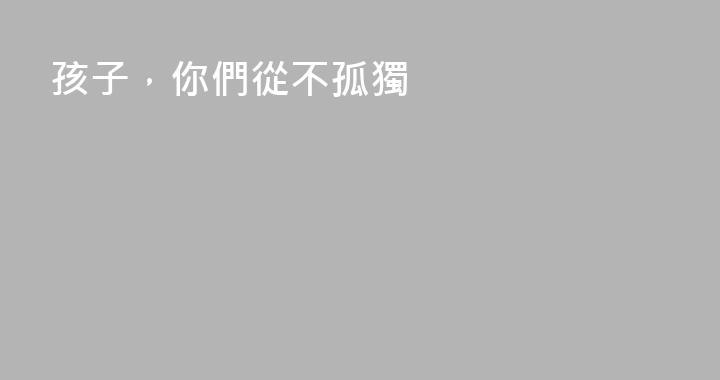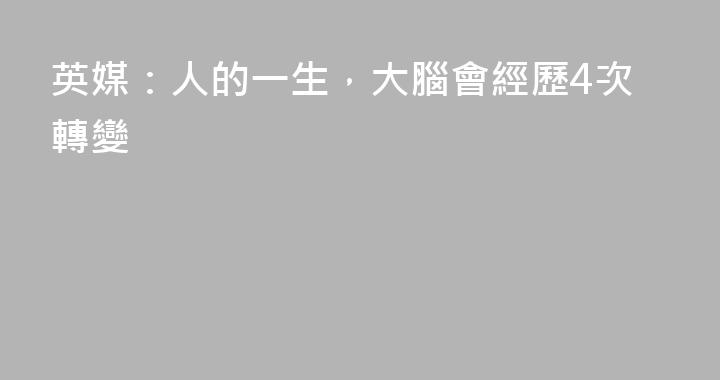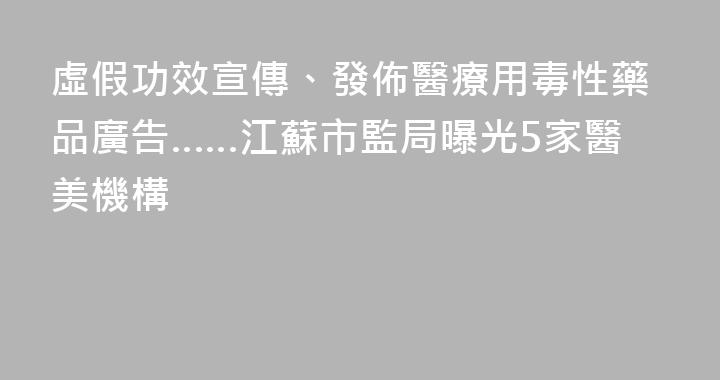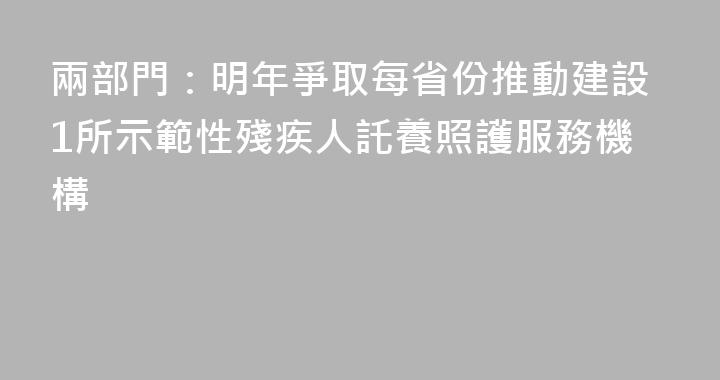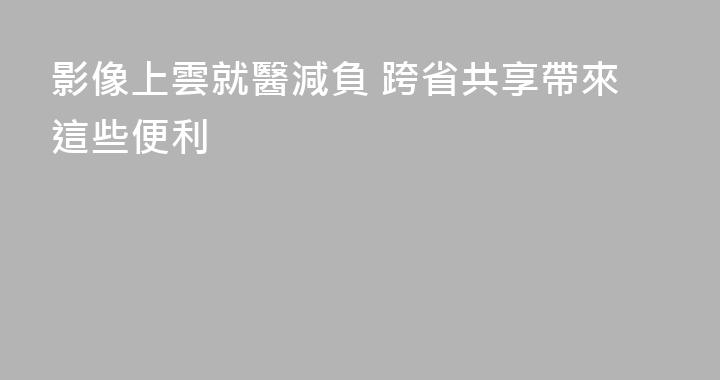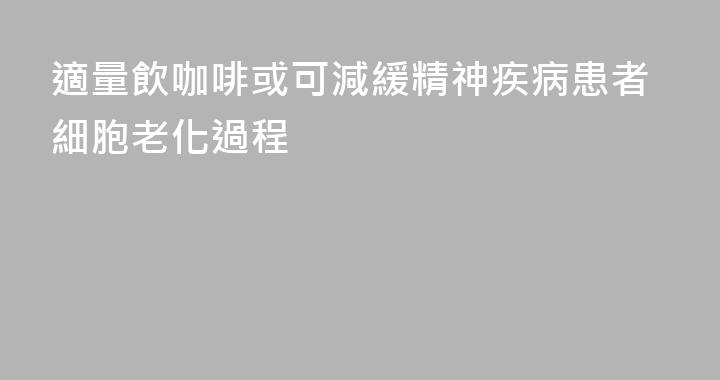【深瞳工作室出品】
採寫:本報記者 吳純新 俞慧友
陳 曦
策劃:趙英淑 滕繼濮
近日,一名遊客在海南省三亞市被蛇咬傷後不幸離世。這場意外引發公衆對抗蛇毒蛋白血清產能不足問題的關注。
其實相較於抗蛇毒蛋白血清,在全球範圍內,有一種藥物更加稀缺——罕見病藥物。已知的罕見病已超過7000種,患者總數超過3億,但其中僅有不到10%的疾病擁有獲批的治療藥物。在我國,罕見病患者人數已突破2000萬,且每年新增患者超20萬。
罕見病不僅種類繁多,而且多數患者病情嚴重、診斷困難。然而,由於患者羣體規模小、藥物研發成本高昂、市場回報有限,製藥企業往往缺乏研發動力。這類藥物也因稀缺而被稱爲“孤兒藥”。
面對罕見病患者羣體,如何打破市場惰性,破解“孤兒藥”的研發與供應困境,已成爲全球性挑戰。
罕見病藥物研發面臨困難
6月23日,湖南長沙一處公園草地上,4歲的男孩佳佳在努力追趕小夥伴們的步伐。
“比起患病初期的笨拙,他現在已經跑得相對輕快了。”佳佳媽媽屈曉燕對科技日報記者說。
佳佳1歲時被確診杜氏肌營養不良症。這是一種因抗肌肉萎縮蛋白缺失而導致的遺傳性疾病。我國目前還沒有治療該疾病的特效藥,只能依賴波尼松等激素藥物延緩病情。
“2023年,國外出了一種迷你蛋白,藥效不錯,但一次性用藥花費高達320萬美元。”屈曉燕說,國外這幾年還研發出幾款“跳躍藥”,對孩子治療都有幫助,可價格都很昂貴。
“天價”藥費,是因爲國內罕見病藥物研發和上市進程緩慢、藥物種類較少,患者不得不依賴高價進口藥物。
創新藥研發是一場耗資巨大、曠日持久的拉鋸戰。通常,一款新藥從立項到上市需要投入超10億美元,歷經10—15年的漫長週期,跨越藥物發現、臨牀前研究、臨牀試驗及獲批上市四個階段。
創新藥研發面臨重重困境,而研發罕見病藥物的難度更大。長期以來,國內藥企對“孤兒藥”研發積極性普遍不高,這背後有多重原因。
“基礎研究能力相對薄弱,國內針對部分致病新基因和機制的原創性研究仍較少,新靶點發現不足,導致早期研發門檻較高。”湖北省罕見病醫學中心主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羅小平說。
亟待完善的患者註冊登記體系,也制約着罕見病的深入研究。罕見病患者數量稀少、分佈廣泛,長期以來缺乏全國性、多中心協同運作的系統化註冊登記平臺。這不利於臨牀研究樣本的組織,也難以形成自然史數據的全面積累。
8年前,南開大學化學學院教授、天津尚德藥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陳悅曾帶領團隊研發腦膠質瘤藥物。然而,他們目前考慮暫停國內臨牀研究,將國內開發重點轉移到小細胞肺癌腦轉移瘤藥物。原因就是肺癌患者基數大,臨牀試驗招募更快,新藥上市更快。這也有利於應對資本寒冬,滿足投資人偏好。
不僅是中國,全球“孤兒藥”研發都面臨類似的困難。
在羅小平看來,企業在投入方面的謹慎很好理解,因爲“孤兒藥”研發成本高、週期長、商業回報不確定。加之我國罕見病研究起步較晚,其藥物研發、引進、生產、銷售等環節,都缺乏足夠支持。
“我們也得兼顧滿足投資人的期望。”陳悅告訴記者,“國外患者較少,但相關藥物上市後的銷售價格通常是普通藥物的數倍以上,因此企業對於在海外研發針對罕見病的新藥,意願要高得多。”
創新藥與仿製藥雙軌並舉
罕見病發病機制複雜多樣,普通藥物很難發揮作用。基於對疾病發病機制的深入研究,創新藥可較高效發揮作用。因此,每一款原研“孤兒藥”的上市,都爲一個深陷困境的罕見病患者羣體燃起了希望之燈。
6月14日,記者走進武漢紐福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實驗室,儀器設備在高速運轉,研發人員正專注於藥品的生產監測。
“我們自主研發的首款1類創新藥紐惟佳,在國內即將完成三期臨牀試驗,預計今年獲批上市。”公司創始人李斌告訴記者,從發起臨牀試驗到現在,他們已走過14個寒暑。紐惟佳是一款治療眼部罕見疾病——ND4基因突變引起的Leber遺傳性視神經病變的藥物。這種疾病多發於14—21歲的男孩,患者表現爲雙目視力受損至失明,目前臨牀上尚無有效療法或治癒手段。
面對國內較長的審批週期,一些創新藥企選擇“先外後內”的全球化開發路徑:佈局全球多中心臨牀,先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美國FDA”)批准的罕見病資格和優先審評券資格證,在海外上市,再引進國內補充臨牀數據,加快在國內的上市進程。
就在2024年底,武漢光谷中源藥業的VUM02注射液獲得美國FDA“孤兒藥”資格認定,這是一種用於治療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藥物。值得一提的是,漸凍症抗爭者蔡磊與中美瑞康攜手推進的第二款小核酸藥物,也獲得美國FDA授予的“孤兒藥”資格。
創新藥研發成本高、週期長,怎樣才能進一步打破患者“無藥可用”的僵局?如果說創新藥是主動“開闢航道”,那麼仿製藥就是“借船出海”。
難治性癲癇作爲一種罕見病,困擾着全國約6萬名患者。此前,其“救命藥”氯巴佔一直依賴限量進口,價格居高不下。2024年底,宜昌人福藥業公司生產的首個國產氯巴佔成功進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這種仿製藥每片的價格僅爲2.11元。
仿製藥的生產提高了藥物的可及性,其通過模仿原研藥的化學結構和藥理作用,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從而顯著降低患者的治療費用。
“雖是仿製藥,但在技術上也有不小突破。”宜昌人福藥業公司總工程師李莉娥說,仿製藥並非簡單的複製,也需要在生產工藝、質量控制等方面進行創新。綜合考慮成本、環保等因素,研發團隊自主設計了全新的合成路線,杜絕了生產過程中的危險工藝。研發團隊對原料藥合成中產生的雜質進行全面研究,充分保障產品安全性,使其產品在質量和療效方面均能達到國際原研水平。
“科普同樣是推動‘孤兒藥’研發的關鍵力量。”湖南省蔻德罕見病關愛中心原總監戴俊武說,“罕見病醫生比罕見病人更罕見。”這背後是醫生對罕見病的關注度和了解程度仍有待提升。讓更多醫生有意識地瞭解罕見病,不僅可以縮短罕見病的診斷時間,降低誤診率,還有助於發現更多罕見病樣本,爲後續“孤兒藥”的研發提供有力支持。
出臺支持政策提升研發動力
隨着我國罕見病患者數量不斷增多,各方對於相關藥物的需求愈發急切。而這些患者中,兒童佔比達到一半。
據統計,2018年至2022年,我國累計批准了43種罕見病治療藥物,涵蓋23種罕見病;2023年,國家藥監局批准了45個罕見病用藥品種,其中18個具有兒童適應證。
記者瞭解到,我國目前政策支持力度持續增強,尤其在兒童罕見病藥物可及性方面已有一定突破。
雖然國內“孤兒藥”的研發在品種覆蓋面、技術路徑和上市效率等方面均有所提升,但相比於發達國家仍有差距。近年來,國家藥監局已出臺多項優先審評政策,但“孤兒藥”的審批機制、超說明書用藥規範等還需進一步完善。“比如,審批路徑仍有優化空間。”羅小平說。
陳悅介紹,國外爲“孤兒藥”設有特殊的政策“工具箱”,可有效提升企業研發動力。
記者瞭解到,過去數十年,美國FDA通過“孤兒藥”認定、快速通道、加速審批、優先審評和突破性療法等五種特殊認定和審評途徑,顯著縮短了治療嚴重疾病和罕見病新藥的研發與審批週期,加快了對嚴重疾病的藥物研發,給患者更快地帶來臨牀獲益。
歐盟則通過“市場獨佔權”實現正向激勵。市場獨佔,通常被認爲是“孤兒藥”研發最重要的激勵因素,旨在平衡新藥創新和仿製藥之間的關係。在歐盟地區,滿足條件的藥品可以獲得10年的市場獨佔權。如果相關產品滿足兒童藥的開發標準,還可以在10年的基礎上再延長2年,以此保障研發企業的創新收益。
“我們可以建立多方共付機制和‘醫保+商保+慈善’分層支付模式,同時優化審批流程和市場獨佔期。”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神經內科主任張如旭說,希望由政府牽頭搭建“罕見病創新聯盟”,聯合藥企、高校和患者組織共建研發平臺。同時,希望政府爲罕見病藥物研發企業提供稅收減免政策。
“改善‘孤兒藥’研發困境,需要多部門協同發力,出臺系統性支持政策。”羅小平建議,加強基礎研究與轉化平臺建設,加大對罕見病致病基因、分子機制、疾病模型等原創性研究的投入,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鼓勵跨學科交叉合作;優化審批與准入機制,借鑑美國、歐盟的立法經驗,完善“孤兒藥”專屬審評審批綠色通道,探索適度的市場獨佔期、稅收優惠和醫保保障等激勵政策。
羅小平還強調,應推動人工智能與前沿技術應用,藉助深度學習模型挖掘非編碼區的致病變異,提高遺傳診斷率,在爲“孤兒藥”研發提供新靶點的同時,提升人羣匹配精準度。
“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某些隱性遺傳病的攜帶者。”中信湘雅遺傳中心主任譚躍球說,對於高度懷疑患有遺傳性罕見病的人羣,應進行遺傳學檢測,明確病因,並在此基礎上指導治療和生殖干預,這將顯著降低家庭中罕見病患兒的再發風險。
目前,我國已發佈罕見病立法相關研究報告。對此,羅小平呼籲,儘快推動罕見病專屬立法的出臺,統籌科研、審批、醫保、用藥指導等多層面工作,讓罕見病患者早日迎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