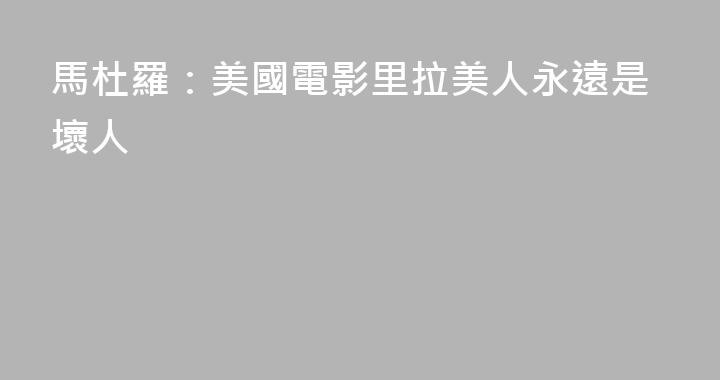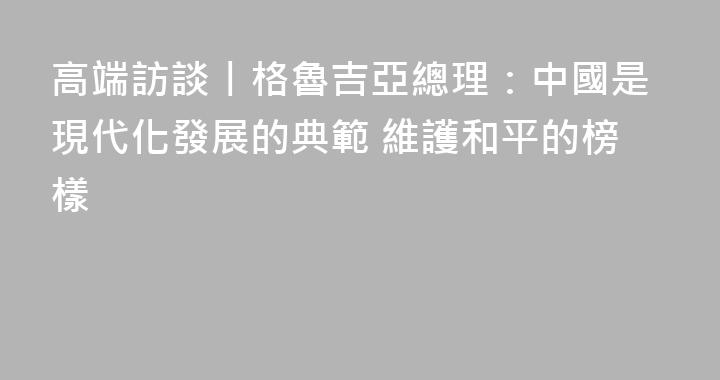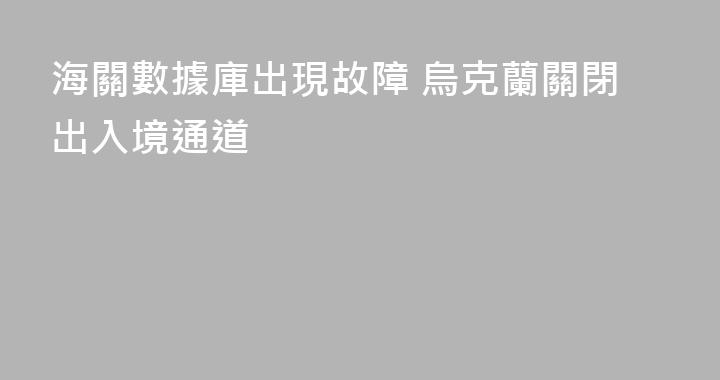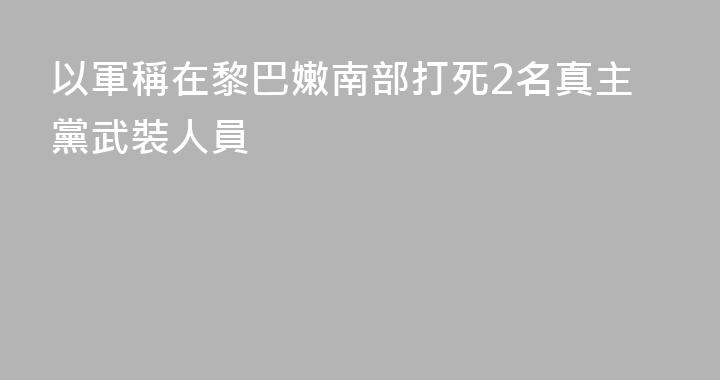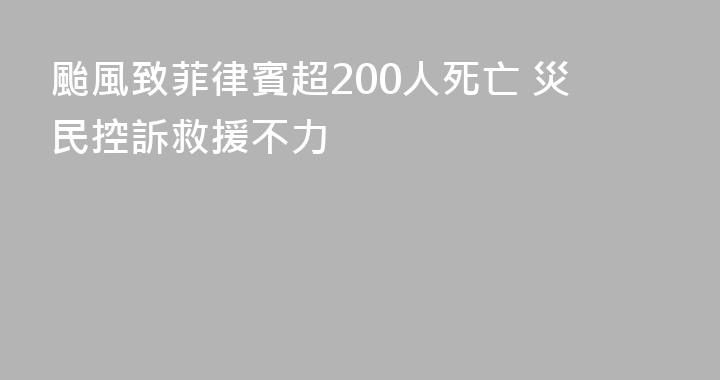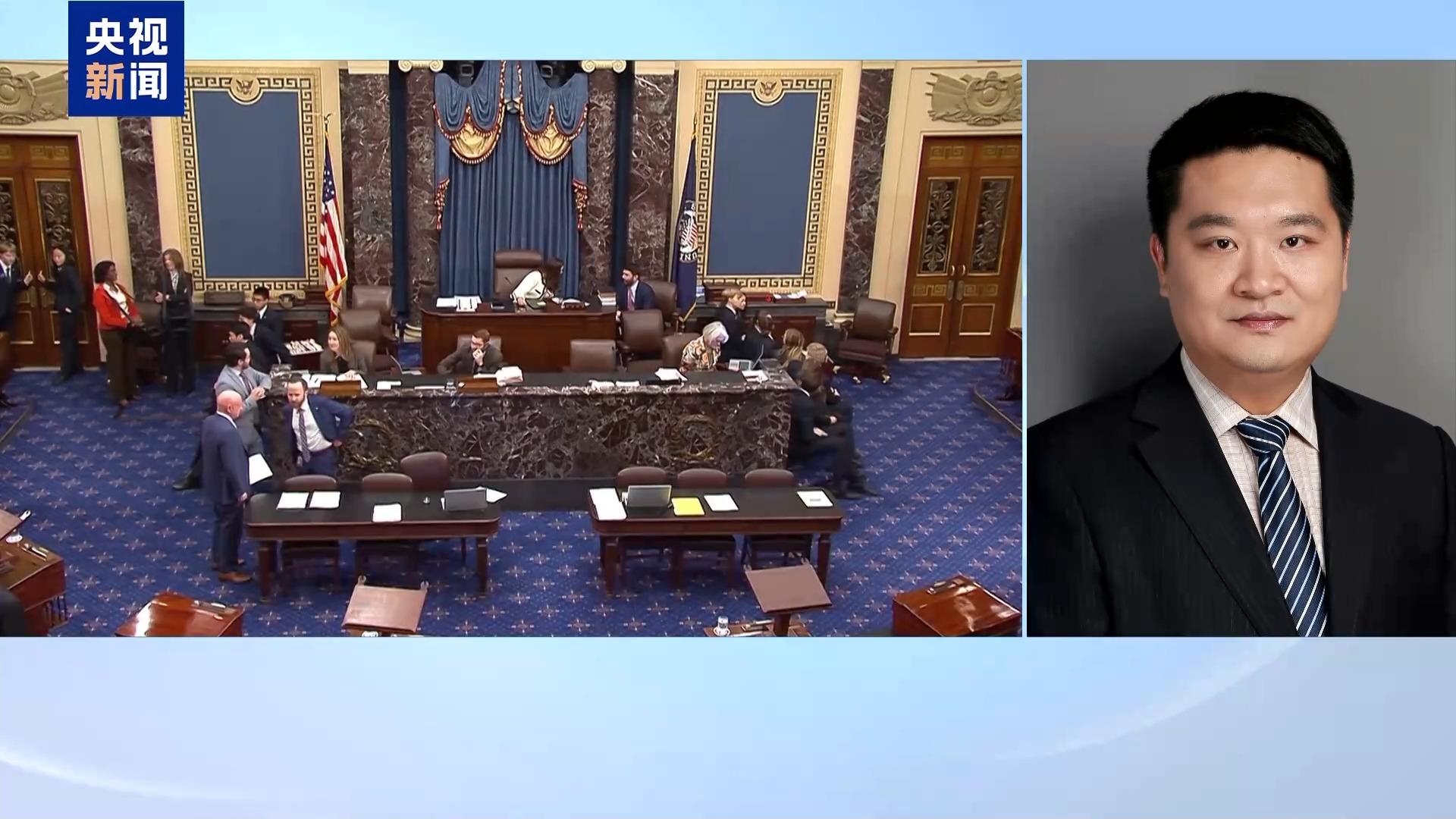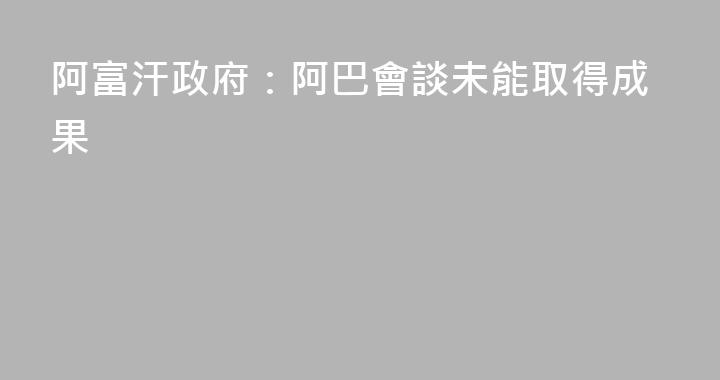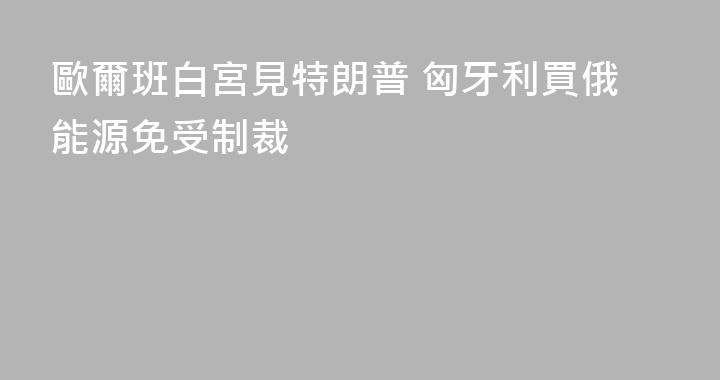【環球時報駐比利時特派記者 牛瑞飛 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木】編者的話:歐盟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與行動正明顯趨於強硬。上週剛結束的歐盟領導人會議聚焦俄烏問題,但27國領導人同時關注加沙脆弱的停火局勢,並探討如何讓該地區實現穩定。盧森堡首相弗裏登在會議期間表示:“歐洲不能只是旁觀,而是要積極發揮作用,這一點至關重要。”儘管內部意見仍不統一、決策機制掣肘依舊,但歐盟在中東問題上的一系列密集表態與行動已傳遞出明確信號——面對加沙局勢持續緊張以及停火協議屢遭破壞,歐盟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呼籲剋制”,而是開始以更具操作性的方式介入地區事務。
“竭力避免在和平計劃中被邊緣化”
“歐盟竭力避免在加沙和平計劃中被邊緣化。”意大利eunews新聞網站25日刊文稱,從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開始,歐盟就是這場衝突的“缺席者”。一邊是美國,另一邊是土耳其、卡塔爾、埃及,而歐盟在過去兩年間對加沙地帶的衝突“束手無策”。不過,隨着美方推進就結束加沙地帶衝突提出的“20點計劃”,未明顯參與的歐盟正急忙試圖發揮作用。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9月中旬在歐洲議會發表講話時首次提出針對以色列的新措施,包括制裁極端主義的以色列部長和暫停部分貿易優惠。隨後,美聯社披露,歐盟內部正討論對以色列商品加徵關稅、凍結部分官員資產,並實施旅行禁令。這標誌着歐盟在以巴問題上首次明確考慮運用經濟和制裁工具。
進入10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聲明,歡迎由美國主導的加沙停火與人質釋放計劃,重申“兩國方案”是解決巴以衝突的可信路徑,並強調歐盟願意參與落實具體安排。而隨後,歐盟對外行動署一份內部文件被曝光,建議歐盟“最大化在加沙的影響力”,爭取加入“和平委員會”機制,在加沙戰後重建與治理中發揮實質作用。同時,歐盟委員會公開呼籲以色列解除對人道援助物資的限制,南歐九國聯合敦促以方“立即開放邊境通道”,顯示歐盟成員國對中東問題態度日趨強硬。
總體來看,歐盟正試圖擺脫過去“出錢不出力”的形象,從單純進行外交呼籲轉向推動政策落實並爭取參與重建。德國IT BOLTWISE新聞網報道稱,歐盟在中東面臨外交困境——儘管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但政治參與不足,歐盟必須重新思考其角色,使其不僅被視爲資金提供者,更應被視爲政治參與者。
一直以來,歐盟在中東事務上強調人道主義援助、尊重國際法和促進地區穩定,以經濟合作、發展支持和外交對話爲主要手段。但現實的衝突和政治博弈不斷提醒歐洲,單純依靠“道義外交”難以應對複雜局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聲稱:“歐洲已基本失去影響力,並展現出極大的軟弱。”
今年8月,歐盟高級官員首次明確使用“種族屠殺”一詞指責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這一前所未有的表態,標誌着歐盟在中東問題上立場的重大轉向。歐洲不願再在中東舞臺上扮演“旁觀者”角色,而希望以政治、經濟及人道多重手段重塑其地區影響力。截至目前,包括法國、比利時、西班牙、愛爾蘭、盧森堡在內的至少過半歐盟成員國已經宣佈承認巴勒斯坦國。
歐盟政策轉向的背後,是多重現實壓力疊加的結果。首先,美國外交重心東移,使歐洲擔憂在中東事務中甚至在更廣泛的國際舞臺上被邊緣化。布魯塞爾不希望完全附和華盛頓,而是希望在價值立場與地區影響之間找到“歐洲聲音”。其次,中東衝突的溢出效應直接影響歐洲安全。難民潮、極端主義、能源供應與糧食安全問題不斷牽動歐洲內政。2025年夏季,地中海難民抵達數量再度上升,令歐盟內部輿論高度關注加沙衝突的外溢風險。再次,歐盟在全球格局中的相對影響力下滑,令其戰略焦慮加劇。“戰略自主”已從外交口號轉化爲現實訴求。最後,歐盟內部政治氛圍也在推動政策變化。歐洲社會對人道問題關注度上升,民間輿論與社會運動敦促政府採取更鮮明立場。多國選舉政治亦推動領導人更重視對外姿態——在這種壓力下,歐盟機構必須展示“能動外交”的形象,以回應民意與輿論。
歷史教訓讓歐盟難以承受
在歷史上,歐洲從未在中東地區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冷戰時期,中東地區的主要外部勢力是美蘇,歐洲共同體雖然嘗試過通過外交協調介入,但缺乏統一聲音。冷戰結束後,歐盟以經貿、人道援助、調停等方式逐步介入中東事務,如在伊朗核問題上,歐盟成功推動簽署2015年伊核協議,即《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
但是,在伊拉克戰爭、2011年“阿拉伯之春”及敘利亞危機中,歐盟影響力相對有限。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歐盟側重於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經濟支持;2016年,歐盟與土耳其簽署難民協議,顯示出歐盟在地區治理中的“危機管控”取向。但在軍事和外交領域,歐盟始終受制於成員國分歧與一致決策機制,缺乏統一行動力。
德國中東問題專家克里斯蒂安·哈內爾特曾在《火環:歐洲如何失去中東並重新奪回它》一書中分析說,中東就像一個燃燒着許多導火索的火環,歐洲在該地區擁有政治野心,但卻“太輕易地屈從於美國賦予它的角色”,爲美國和平進程提供資金。此外,歐洲也誤判了中東的局勢,比如“阿拉伯之春”就讓歐洲措手不及——因爲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一直專注於打擊恐怖主義——其結果對整個歐盟來說是“難以承受”的。
德國之聲報道稱,雖然歐盟在伊核協議的達成中發揮了作用,但自2018年美國宣佈退出該協議以及用於促進同伊朗進行非美元交易的INSTEX支付機制崩潰以來,歐盟在對伊朗貿易中缺乏強大的經濟籌碼。
與此同時,歐盟內部的分歧也是繞不開的問題。這既源於歷史文化差異,也與現實利益密切相關。基於宗教與歷史情感、能源、貿易等不同方面的考量,歐盟各成員國與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並不相同。德國、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等國傾向於謹慎處理與以色列的關係,強調安全與歷史責任;而西班牙、愛爾蘭、瑞典、比利時等國則更爲積極,呼籲對以方行爲採取限制措施,並推動承認巴勒斯坦國。法國則力求在外交調解與現實利益之間保持平衡;意大利與希臘則更關注移民與能源通道安全。這種“多聲部外交”使歐盟在每次重大危機中都難以迅速達成統一立場。
此外,歐盟的對外政策需要27國一致同意,決策過程往往趨於妥協和保守。即使在輿論與人道壓力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要達成一致行動仍面臨結構性障礙。
不過,據《環球時報》駐比利時特派記者觀察,歐盟成員國近年來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緩和跡象。一方面,人道危機與衝突外溢促使更多國家認識到“保持沉默的代價”;另一方面,歐盟委員會與對外行動署正通過機制創新推動政策協調,例如審查歐以協會協議、研究貿易限制等手段。這些努力雖未徹底消除分歧,卻表明歐盟在逐步形成更具行動力的共同立場。
正嘗試通過多層次手段進入中東
“歐洲必須在中東事務中擺脫旁觀者角色。”西班牙政治家、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今年6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刊文稱,歐盟需要爲解決巴以衝突制定更加強有力的計劃。“歐洲尋求在加沙發揮作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道稱,歐盟是巴勒斯坦最大的援助捐助方,同時也是以色列最大的貿易伙伴,這種“中間者”位置凸顯了歐盟的潛在影響力。
歐盟正嘗試通過多層次手段進入中東。一是強化與阿拉伯國家的合作。歐盟深知,若想在地區擁有影響力,必須依託區域夥伴。近年來,歐盟與埃及、約旦、沙特、阿聯酋等國的政治與經濟對話顯著加強。去年3月,歐盟與埃及的雙邊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重點支持埃及經濟復甦、阻止非法移民,並確保地中海天然氣供應安全。歐盟與約旦、黎巴嫩等國的合作則集中於難民安置與人道援助。通過發展合作、氣候項目和綠色轉型投資,歐盟正努力構建“合作穩定圈”,以經濟紐帶增強政治話語權。
二是藉助國際法與多邊機制,維護規則秩序。歐盟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政治解決,反對任何單邊改變現狀的行爲。無論在加沙、敘利亞,還是也門問題上,歐盟都強調國際人道法的不可侵犯性,呼籲設立國際調查機制。通過“規則塑造力”,歐盟希望在道義與法律層面確立地區影響。
三是以經濟和政治工具施壓。歐盟是以色列及阿拉伯國家的重要經貿夥伴,擁有制裁、援助、市場準入等政策槓桿。上個月,歐盟委員會首次提出暫停部分對以色列的貿易優惠,以此作爲政治信號;同時,布魯塞爾也在研究將援助資金與衝突緩和掛鉤的機制,以實現“援助有條件、合作有約束”的政策轉型。
四是倡導“意願聯盟”機制。面對一致決策的限制,一些國家積極主張建立由志同道合成員組成的“先行機制”,在外交表態、人道援助或停火倡議上率先行動。西班牙、愛爾蘭、比利時已多次倡議形成“行動小組”,推動歐盟在聯合國層面統一聲音;法國和德國則探索通過歐盟框架外的合作機制,推動實現地區穩定。雖然這種方式難以替代歐盟整體政策,但在實際行動上能爲歐盟外交注入靈活性。
歐盟在中東的“角色轉型”,既是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必然結果,也是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現實選擇。歐盟的目標,並非通過軍事幹預主導局勢,而是以“規則、合作、援助”的綜合力量,在中東塑造一種可持續的和平秩序。面對複雜多變的中東局勢,歐洲能否真正實現“從呼籲到行動”的跨越,取決於它能否在內部凝聚共識、在外部贏得信任。